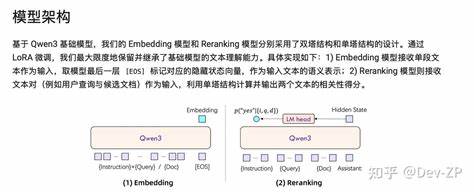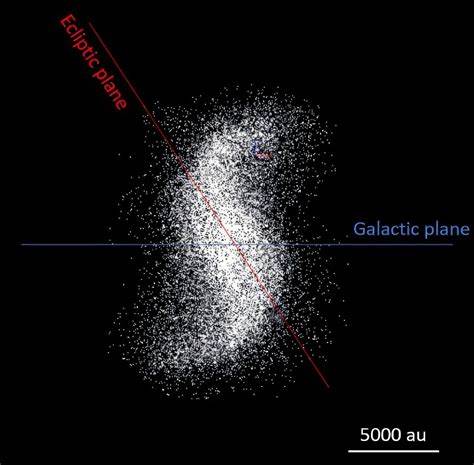2025年6月5日,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支持了一位直女性员工马琳·埃姆斯(Marlean Ames)在就业歧视诉讼中的权利。法院明确指出,作为多数群体成员的原告在职场歧视案件中,不应承担比少数群体更苛刻的举证责任。这一裁决不仅纠正了联邦上诉法院长期以来对“多数群体”原告设置的特殊障碍,也为职场性别歧视和多样性政策带来了深远影响。该案件的裁决对于如何理解和适用《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Title VII)关于性别和性取向歧视的规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马琳·埃姆斯是一名在俄亥俄州青少年服务部工作多年的资深员工,她曾负责监测和应对监狱内的性侵问题。尽管工作经验丰富,她经历了两次升职失败,最终被替代的都是较为年轻且职位资历较短但性取向为同性恋的员工。
埃姆斯认为,这种情况背后存在基于其性取向和性别的就业歧视。值得注意的是,最高法院于2020年已裁定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属于基于性别的歧视范畴,从法律角度扩大了受《民权法案》第七条保护的范围。在这起案件中,联邦上诉法院认为,作为一名直女性,埃姆斯必须额外提供所谓“背景情况”证明,以表明其雇主是一家“反对多数群体”的雇佣方。具体来说,需要她通过证据显示决策人中存在少数群体成员或利用统计数据证明其公司的用人数据显示歧视倾向。然而,埃姆斯未能满足这一附加条件,导致她的诉讼在上诉阶段败诉。最高法院此次推翻了这一要求,强调法律文本并未对多数群体与少数群体的原告设置不同保护级别。
大法官杰克逊(Ketanji Brown Jackson)撰写的多数意见指出,法律保障的是所有个人的平等权利,无论其是否属于社会中的少数群体或多数群体。因此,法院拒绝允许司法系统制造以群体身份划分的歧视诉讼门槛。此判决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即任何个人在遭遇职场不公时,都应享有同等的诉讼便利和平等保护,不因自身所属群体的社会地位不同而被设立额外困难。该案的审理和判决背景复杂且具有社会政治意义。两年前最高法院曾推翻高等教育中的种族考量录取政策,体现了对优待措施日益严峻的审查态度。而特朗普政府时期的大力推动清除多样性及平权项目也为本案提供了微妙的政治环境。
尽管如此,拜登政府支持埃姆斯的立场,向最高法院提交了支持原告的法律意见书,反映出当前政治力量对多样性保护和反歧视政策的不同态度。值得注意的是,大法官托马斯(Clarence Thomas)和戈萨奇(Neil M. Gorsuch)发表联名意见,侧重探讨如何界定“多数群体”的难题。托马斯指出,社会中群体身份复杂多变,性别、种族、宗教和地域因素交织,使得“多数”与“少数”的划分并非绝对。例如,女性在全国人口中占多数,却在某些行业或地区为少数。托马斯还批评了对“反多数歧视”的假设过于武断,认为现今许多企业实施的多样性与包容政策,实际上可能导致针对所谓“多数”群体的歧视,这凸显了当前职场治理的复杂性和挑战。这次最高法院判决还呼吁企业、司法机关和社会对职场公平的理解应回归法律原意,即人人平等保护,避免人为制造隔阂和额外障碍。
这对雇主如何设计岗位晋升、薪酬待遇和解雇决策带来了警示。在性别歧视和性取向歧视不断被明确纳入法律框架的今天,仅仅因为某员工属于所谓“多数”群体便加重其诉讼负担,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也不利于社会和谐与法律公平。这起案件和判决结果以其社会重要性、法律创新性和现实意义备受关注。它不仅保护了个体权利,也促使劳动法的实施更加精准和公平,推动建立无歧视、机会均等的职场环境。专家普遍认为,该裁决将成为今后职场歧视案件中反复引用的重要法律依据,促使更多雇主重新审视其多样性和反歧视政策的合规性。此外,裁决也可能促进立法机关对现有反歧视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和细化,为社会各界提供更明确的遵循框架。
总的来看,最高法院对埃姆斯案的裁定是美国职场反歧视实践中一次重要进步。它推动了法律保护范围的平等化,消除多数群体原告被不公平对待的司法障碍,同时也挑战了社会传统的身份认同分类思维。未来,这一判例将激发对职场多样性、公平性以及包容性的更深入讨论和创新探索,为构建更加公正和平衡的工作环境奠定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