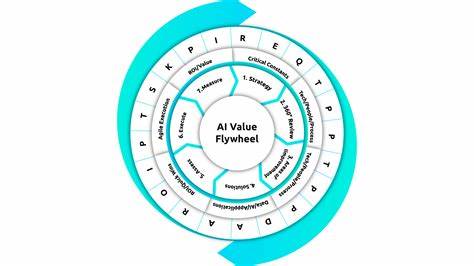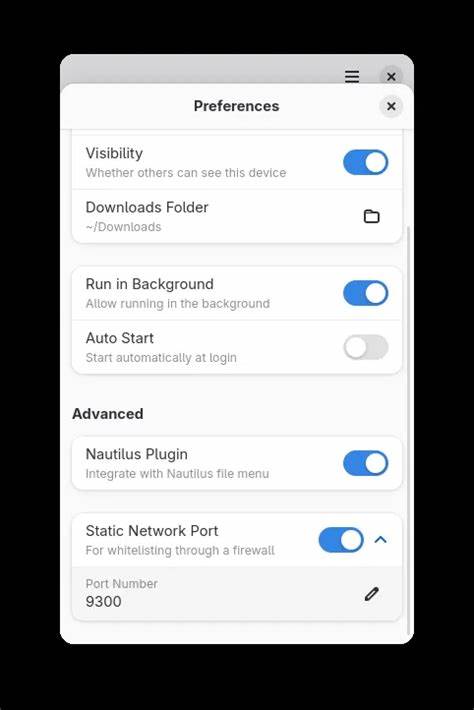德州达拉斯曾是美国最后几个中产阶级家庭还能负担得起住房的城市之一,然而如今的现实却截然不同。尽管当地的土地价格相对低廉,且政府规章制度并不严苛,但住房价格却经历了显著的飙升。向深层次剖析后发现,造成这一现象的核心因素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城市规划或土地使用政策,而是大型房企和私募股权资本对房地产市场的深度介入和强力操控。 长期以来,美国住房的理想是实现广泛的财产所有权,使居民不仅拥有自己的房屋,更肩负起对社区和社会的责任感。过去,小规模的地方承包商和家族企业能够灵活应对市场需求,利用本地储蓄机构和社区银行的信贷支持,稳步推动房屋建设。而这份结构原本形成了美国房地产市场多元且竞争激烈的格局,也保障了住房供应的及时和平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尤其是储蓄与贷款机构(S&L)危机改变了这一局面。政策制定者未选择恢复这些机构在本地住房市场的核心作用,反而推动华尔街大型金融机构大规模介入房地产资产。由政府设立的资产处理机构将数百家破产的S&L的房地产资产以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给私募股权基金、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华尔街实体,促成了一场财富的巨额转移。原本由本地信贷支持的小型房屋建设者因此失去了资本来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 随之而来的便是房企的合并浪潮。一批大型、上市的全国性房企如D.R. Horton、Lennar 和Pulte Group在达拉斯-沃斯堡都市圈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以高昂的价格收购中小型建商,打造出寡头垄断式的市场结构。
这些巨头不仅占据了更多的建筑市场份额,更通过金融手段锁定了产业链上下游资源,包括建筑材料供应商和分包商,挤压了小型建商的生存空间。 大型房企所享有的资本成本优势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壁垒。他们设立了自有的抵押贷款公司,为购房者提供低于市场利率的贷款,诱导买家以更高的价格购房。相比之下,中小建商因融资难度大,无法提供类似的优惠,导致他们不得不以较低价格出售房屋,失去竞争力。贷款利率的人为压低同时抬升了房屋售价,进一步推高了当地的房地产估值,并使得土地和建筑成本水涨船高。 这不仅令普通购房者望尘莫及,也使得整个市场的住宅供应严重不足。
达拉斯多年来新建住房数量持续低于市场需求,估计短缺的住房单位数一度超过12万套,远高于加州的缺口水平。与此同时,房地产投资者,尤其是私募基金,开始大规模入场买断单户住宅,将这些房产转为出租用,进一步限制了市场上的待售房源,推高租金水平,导致城市住房更加不可承受。 此外,达拉斯地区的房屋转售市场也遭到扭曲。私募股权和机构投资者手持大量物业,通过竞拍推高价格,令一般家庭进入市场的门槛增高。疫情期间,由于利率上涨,业主们不愿出售手中拥有的低利率房产,进而造成二手房供应骤减,供应缺口和价格上涨双重压力加剧了住房负担危机。 背后的金融体系已经将住房视为一种可交易的投资资产,而非简单的居住空间。
这种转变导致了一种“租赁社会”的兴起,在这个社会中,房屋多数由资本运作而非家庭所有,房价因金融投机和市场操纵而一路攀升。与之匹配的是几位新晋的房产富豪,他们通过市场垄断赚取了巨额利润,而中产阶级家庭则越来越难以实现买房梦。 针对现有状况,专家建议必须从根本上调整房屋建设和金融融资的政治经济结构。首先,应采取措施限制大型机构,特别是华尔街私募基金对单户住房市场的过度集中和操纵,防止房屋被纯粹作为金融资产炒作。其次,重塑地方信贷体系,重新赋予社区银行和本地储蓄机构为小型建商提供贷款的能力,降低融资门槛,支持本土多样性的房屋建设力量。第三,打击大型建商利用规模优势排挤竞争、操控价格的行为,还原健康竞争环境。
虽然放松地方土地使用和建筑代码的限制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小型建商,但在寡头垄断和资金集中控制的背景下,其作用受到严重限制。没有金融与产业链的结构性改革,单纯的规章修改难以扭转市场垄断态势和房价攀升的大趋势。 达拉斯的经验告诉我们,住房危机和高房价并非蓝州与红州简单区别的产物,而是美国全境深层的金融资本集中与市场寡头化的表现。疫情后房价飞涨、租金上涨,乃至社会不平等加剧,实质上是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和垄断力量作祟的直接结果。 未来,如果不重新确立以社区和家庭为核心的住房理念,真正把住房还给需要它的人,政策只会进一步助长投机资本,将住房变为无法企及的奢侈品。只有破解金融资本对建筑产业链的控制,重建多元化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结构,美国的住房负担问题才有望迎来转机。
德州达拉斯的案例成为警示,提醒所有城市和政策制定者:住房难题背后,金融与产业寡头才能是解决方案的关键所在。抓住这点,方能为亿万家庭筑起真正的“居者有其屋”的美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