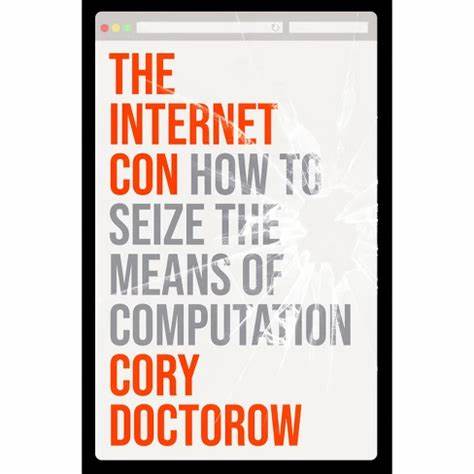公海,也被称为国际水域,占据了地球海洋61%的面积,覆盖了43%的地表,实际上构成了地球生物圈体积的三分之二。尽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公海长期以来面临着严重的人类活动压力,特别是过度捕捞和即将展开的深海采矿活动。保护公海免受一切形式的资源开采,成为全球海洋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公海的生态系统极为复杂且独特,栖息着多样的海洋生物,包括巨型海洋动物如鲸类、海龟、鲨鱼和金枪鱼等。这些物种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保持着生态系统的平衡。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公海生态系统面临着氧气耗竭和营养物质减少的严峻挑战,这一现象使得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
长期以来,公海资源的无序利用已导致某些物种数量急剧减少,鲸类捕猎从17世纪开始,直到20世纪中期,诸如鲨鱼、鱿鱼等多种鱼类被大规模捕捞,令海洋生物资源显著衰退。而科技进步带来的深海采矿计划,则对本就脆弱的海底生态系统构成了全新威胁。公海不仅是丰富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更是全球气候调节的核心环节。海洋在碳循环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地球上最大的碳汇。海洋生物通过“生物泵”和“养分泵”两大机制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到深海中。生活在中层水域的无数鱼类和无脊椎动物会在夜间游向水面觅食,白天则回到深海排泄碳含量丰富的废物,使碳得以长期储存在深海中。
若无这一机制,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极有可能高出200ppm,地表温度可能增加约3摄氏度,后果不堪设想。与此同时,养分泵的作用也十分关键。生物体的粪便和死亡遗骸从浅层沉降至深层,随着海水层间分层加剧,表层海水营养荒漠化愈发严重。诸多大型海洋动物通过深潜觅食后排放养分于表层,促进了浮游植物及其他生物的生产力,从而支持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繁荣。然而,数百年来的捕猎尤其是捕鲸产业的蓬勃发展,严重扰乱了这一自然循环。20世纪中叶以后,公海捕捞活动更是扩展至众多鱼类和软体动物,渔业补贴刺激了渔船数量的激增,捕捞强度显著提升,许多鱼类资源濒临枯竭,海洋生态系统损害严重。
公海捕捞不仅影响渔获物种本身,更带来严重的副渔获问题。无数非目标物种如海鸟、海龟、鲸类被渔具误捕或捕杀,生态系统遭受连锁破坏。部分使用的渔具,如漂浮的鱼聚集装置,误捕率极高,导致众多海洋生物非故意死亡。此外,过度捕捞与海洋缺氧相结合的问题逐渐显现。全球海洋含氧量在过去数十年中已经减少2%,深海变得更加难以支持高需氧物种,这不仅让鲨鱼、金枪鱼等鱼类聚集至更浅水域,增加被捕几率,也导致它们生长缓慢、体型缩小,繁殖力下降,这种恶性循环加剧了渔业的脆弱性。即便在捕捞之外,公海的资源开采威胁也日益严峻。
深海采矿作为一种新兴工业,正试图从海床开采多达数种金属和矿物资源。这些矿物对制造绿色能源设备十分关键,但深海采矿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样巨大且无法预测。采矿活动会摧毁海底生物栖息地,引发大量沉积物流失,影响海洋底层及周边生态系统的氧气和营养循环。更为致命的是,深海矿床中的有机碳若被扰动,将可能释放数千年累积的碳,反而加剧气候变化问题。当前,国际海床管理局在深海采矿政策的制定上存在利益冲突,同时监管缺乏透明度和有效执行,难以保障海洋环境不受损害。面对公海的种种威胁,2023年联合国达成了《公海条约》,旨在填补国际治理的空白,推动设立更多海洋保护区,计划到2030年实现30%的全球海洋保护目标。
然而,条约的生效和实施仍取决于60个国家的批准,至目前为止仅28国完成批准程序,条约的具体机制尚待完善,执行进程缓慢。鉴于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危机的紧迫性,守护公海生态不可再拖延。彻底停止在公海范围内的捕捞、深海采矿及石油天然气开发成为最具远见的选择。关闭公海捕捞并不会影响国际航运、科学研究及非消耗性的活动。相反,这将为全球海洋生态系统带来拯救性的复苏机会,使得跨界鱼类种群得以恢复,滋养邻近国家的专属经济区。更重要的是,保护公海有助于确保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促进气候调节,为后代留下一片健康的海洋。
经济层面上,公海捕捞依赖于政府大规模补贴,捕捞利润并不真正可观。将保护资源转移到国家沿海经济区,有助于促进更公平的资源分配,提升全球尤其是中低收入国家的渔业收益。深海采矿则完全缺乏可持续性基础,目前陆地上的矿产资源更加丰富且易于管理,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绿色技术减少对于深海矿物的依赖。因此,深海采矿无论从环境、安全还是经济角度考虑,都不应成为未来的选项。历史告诉我们,过度开发往往带来灾难性的生态崩溃,但公海仍有机会成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典范。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形成全球共识,建立强有力的保护机制,才能确保公海的资源永久不被挖掘利用,带来生态、气候和社会的多重效益。
正如20世纪五十年代全球共同保护南极大陆一样,如今保护公海的决策关系着全人类的未来。让我们勇敢担当起来,携手守护地球上这片最浩瀚、最深邃的蓝色心脏,将它作为人类和自然共同的遗产,永远免受掠夺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