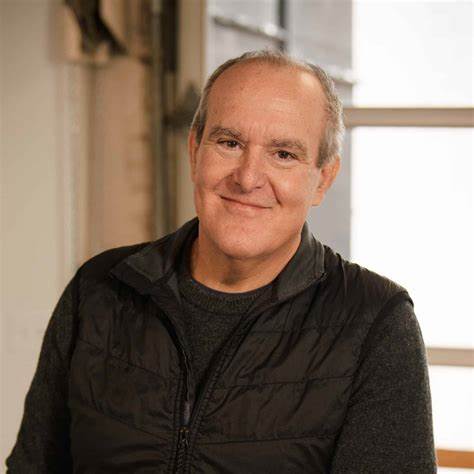公海,作为国际水域,是地球上最广阔、最神秘的海洋区域,占据了全球海洋面积的61%,覆盖了地球表面约43%,几乎构成了地球生物圈的三分之二。尽管其广袤无垠和丰富的生态系统赋予了公海极其重要的环境价值,但由于历史上的过度捕捞以及日益增长的工业开采压力,这片海域正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威胁。保护公海免受一切资源开采,成为全球生态治理中不容忽视的一项紧迫任务。 公海的生态功能和气候调节作用举足轻重。作为地球表层最深的区域之一,公海平均深度达到4100米,是世界最大的碳汇,承担着吸收和储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关键任务。海洋生物通过所谓的“生物泵”和“营养泵”维系着碳循环和平衡气候。
众多生活在中层海域(约200至1000米深度)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每日进行垂直迁徙,夜间在表层觅食,白天回到深水区排放含碳排泄物,从而有效地将碳固定到深海,防止其重返大气。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可能会高出200ppm,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3摄氏度。 然而,公海的生态系统正在遭受严重破坏。自17世纪的捕鲸时代起,公海生物资源便受到人类的持续剥削。20世纪中叶以后,远洋捕鱼业迅速扩张,捕捞对象从鲸鱼转向鱼类、鲨鱼和鱿鱼等海洋生物资源。如今,技术的进步和经济利益驱动下,捕鱼活动延伸至更深海域,且深海采矿的计划不断增多,威胁着海底的生态环境。
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更是降低了海洋的生产力,海水变暖、氧气缺乏和养分流失使得许多海洋物种面临生存挑战。 尽管如此,当前全球保护公海的努力依然不足。公海保护区的面积不到1%,主要原因是缺乏有效的国际法律和治理机制。尽管2023年联合国高海洋条约通过,为公海保护建立了制度框架,但距离其全面生效仍需多个国家的批准和执行。条约的实施复杂性以及国际多边协作的难度,使得保护行动进展缓慢,迫切的气候和生物多样性危机亟需我们采取更具前瞻性的政策。 公海中的渔业活动问题尤为突出。
估计有3500艘渔船在公海作业,很多依靠政府补贴维持经济活力。补贴不仅扭曲了市场竞争,更导致过度捕捞。鱼类资源的稀缺使得捕捞行业利润微薄,且部分船员面临强迫劳动等人权问题。高强度的捕捞造成标志性海洋生物大量死亡,例如信天翁、海龟和鲨鱼等濒危物种数量骤减。此外,使用引诱装置的大规模围捕方式,甚至拖网对海底生态也造成巨大破坏。 深海捕鱼所带来的生态风险同样不可忽视。
中层海域的微小鱼类对生态系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大型鱼类和海洋哺乳动物提供丰富食物资源。大规模捕捞将破坏食物链,引发连锁反应。加之海洋缺氧现象日益加剧,捕捞压力使得受影响物种迁移至更易被捕获的浅层水域,导致种群再生率下降,生态系统稳定性遭破坏。 针对公海的深海采矿计划更是潜在的灾难。虽然目前尚未开始商业化采矿,但已有三十多份探索合同,且部分国家和企业推动加快采矿审批,监管体系缺乏透明度和独立性。深海矿产资源的开采将扰动海底沉积,释放有机碳,导致沉积物增加,氧气进一步耗竭,可能带来无法逆转的生态影响。
相较于陆地矿产,深海矿物含量低且分布分散,开采成本高昂,环境代价巨大,且难以进行有效的环境监测、修复和赔偿。 与深海采矿相关的绿色技术行业声称需求不可或缺,但实际上,陆地矿山资源丰富且更加易于监管。技术进步也在促使绿色能源向更低矿产依赖转型。科学家和环保人士呼吁依据预防原则,全面暂停深海采矿活动,防止对全球海洋系统构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保护公海并非只关乎生态,更关涉全球公平与社会正义。资源贫乏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很难参与远洋捕捞行业,因此维持现有的开采权利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
关闭公海捕鱼后,这些国家可在本国水域实现更合理的渔业管理和资源利用,带来更广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此外,实施高水平保护的海洋区域能够显著促进跨境物种的恢复,提升全球海洋的生产力和多样性。 公海的保护不会影响国际航运、旅游或合法科学研究,包括生物探索,因而是平衡多方利益的可行方案。借鉴20世纪50年代国际社会为保护南极大陆所达成的协议,可以建立类似的全球公海保护体系,确保海洋这一全球公共财富的可持续利用。 尽管当前没有明确的政治路径快速实现公海全面禁采,但科学界、环保组织及多个国家已经联合发声,推动国际社会加快行动。延误只会使生态破坏更加严重,恢复代价更高。
保护公海,是逆转全球气候变化趋势、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海洋公平的关键一步。 因此,最明智的选择是在公海永久禁止所有形式的资源开采,包括捕鱼、海底采矿、油气开发等。采取这一行动缘于对科学事实的尊重,对未来世代的责任感,以及对地球生命系统的深刻认识。让我们团结起来,共同守护这一蓝色宝藏,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