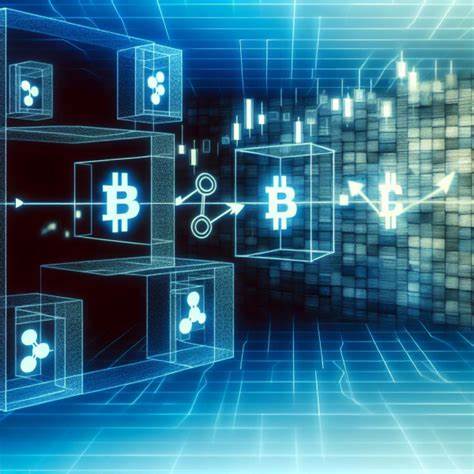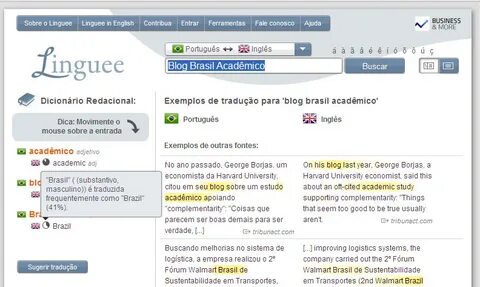十九世纪末,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对工业化城市扩张的观察中写下了一段惊人的预言:城市中心的劳动者住房会因土地价值的人为提升而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商店、仓库和公共建筑,工人被迫迁往城市边缘。近百五十年后,我们称之为绅士化或士绅化的过程,几乎复刻了恩格斯的描述。把恩格斯的历史性洞见放在当下,有助于理解为何现代城市在财富聚集与空间排斥之间不断拉扯,以及我们可以如何重塑城市治理以保障更多人的居住权利。 恩格斯的核心论点可以用马克思主义城市经济学的两个概念来概括: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使用价值指的是居住地为居民提供的生活、工作与社交功能;交换价值则是土地或建筑在市场交换中的价格潜力。资本化程度提高时,交换价值往往成为主导权衡。
城市中心、交通枢纽、公园周边等具备高交换价值的地段,容易被资本视为更高盈利的对象,低价住宅和以社区为中心的用途因此遭受替代压力。 现代绅士化并非偶发的社会现象,而是由多重制度性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金融化使得土地和住房成为全球资本配置的对象,不仅本地开发商,跨国投资者、房地产信托基金与养老金都参与其中。税收政策、私有化浪潮、城市为争取"优质税基"所采取的招商和规划导向,进一步把城市治理变为"增长机器"。在这种逻辑下,城市的成功被衡量为吸引高收入人群、企业和资本的能力,而非居民的生活质量。 以旧金山为例,高科技产业与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市中心和便利交通沿线的土地价值飙升。
本地长期居民面临租金上涨、房屋被改建为短期租赁或豪华公寓、社会基础服务向高端需求倾斜等一系列连锁反应。纽约市的许多社区同样经历了零售市场高端化、艺术家和小微企业被驱逐的过程。伦敦的"金融中心化"与大量外国买家导致的空置高端住房也体现了类似逻辑。城市空间的价值被重新定义为可以被买卖和投机的资产,而非仅仅是居民的生活场域。 绅士化的影响远不止个体居住选择的改变。它侵蚀城市多样性,削弱基层商业生态,破坏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与文化记忆。
低收入和中产阶级的外迁往往带来更长的通勤、更高的生活成本和更脆弱的社会支持体系。公共资源的配置也可能发生偏移,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逐渐优先服务于高消费人群,进一步加剧空间不平等。 理解绅士化的机制,有助于寻找制衡策略。政策工具可以分为抑制投机、保障居住权和重构土地与开发收益的分配三类。抑制投机需要从税制入手,例如对空置房产或短期投机行为征收更高的税率,增加土地持有成本,从而降低资本通过囤积来提高价格的动机。另一个重要手段是加强透明度和监管,限制不透明的海外投资和复杂的金融产品对本地住房市场的冲击。
保障居住权的措施包括租金管制、长期租约保护、反驱逐法律与扩充公共住房供给。租金管制可以在短期内为既有居民提供缓冲,但设计上需避免产生供应紧缩或抑制新建租赁住房的副作用。社区土地信托作为一种常见的实践,通过将土地所有权从市场中剥离,保障住房长期可负担性与社区自治,是在实践中被广泛讨论的模型。合作式住房、非营利开发项目与政府主导的社会住房也能在不同规模上发挥作用。 重构土地与开发收益的分配意味着城市在允许高利润开发的同时,应当通过政策确保公共回报。征收开发增值税、实施包含性分成(如强制性保障性住房配比)、土地价值回收机制与地方基础设施税,可以把私人成交的增值部分转化为公共财政,用于城市住房、交通与社会服务的再投资。
通过这种方式,城市可以缓解因地段升值而带来的社会成本。 社区参与与民主规划是对抗绅士化的关键维度。单向的"城市招商"政策往往忽视基层声音,导致开发结果与公共利益不符。强化参与式预算、在规划许可过程中引入受影响居民的约束性意见权,以及确保透明的利益相关方信息披露,有助于建立更具正当性和可持续性的城市发展路径。草根组织、租户联盟与社区联防机制在许多城市中已展现出强大的动员与谈判能力,是保护既有居民的重要力量。 同时,必须认识到绅士化并非能够通过单一政策彻底根除的现象。
它与全球化、技术变迁、劳动力市场结构、人口迁移等更广泛的社会经济趋势交织在一起。因此政策组合需要灵活而长期的视角,兼顾短期的居住保障与长期的土地制度改革。改革土地制度并非简单之举,但通过逐步扩大公共或非营利性土地持有、改进土地税制与强化对短期投机行为的监管,可以逐步重塑土地价值的分配逻辑。 学术界与公共讨论也应超越"居民搬迁即失败"的简单结论,关注更深层的制度性选择与权力结构。例如,为什么一些城市选择以招商引资和高端开发为核心增长策略?这些选择背后往往涉及财政压力、地方官员的政治考量与评价体系、以及债务与评级机构的约束。理解这些制度约束有助于设计更具系统性的改革方案,例如调整地方政府对经济成功的衡量标准,将社会福利、可负担住房比例与生态韧性纳入绩效考核。
历史告诉我们,恩格斯的警告并非宿命宣判,而是对制度选择后果的敏锐洞察。城市政策并非自发出现的市场结果,而是政治力量与制度安排的产物。通过政策工具组合的优化、社区主体性的强化以及对土地价值再分配机制的创新,城市仍有可能走出以交换价值为唯一准则的窘境。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把短期的财政与增长需求,与长期的社会公平与城市可持续性结合起来。 面向未来,城市治理需要更平衡的价值观。当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确保城市既是生产资本的载体,也是承载人民生活的家园,是每个城市决策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恩格斯的文字提醒我们,若不主动干预土地与住房的市场规则,城市将持续成为财富再生产的场域,同时也将不断制造新的隔离与不平等。积极的改变要求政策制定者、社会力量与学术界共同参与,探索能够把城市价值回归到公共利益与民主治理的平台与机制。 在全球城市化继续推进的今天,借鉴恩格斯的历史视角并结合当下经济与科技现实,我们可以更清晰地识别绅士化的驱动力与后果。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汲取经验,推动政策创新与社会动员,争取一个更具包容性与正义性的城市未来。城市不应只是资本的增值机器,而应首先是人们的生活场域与共同体的载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