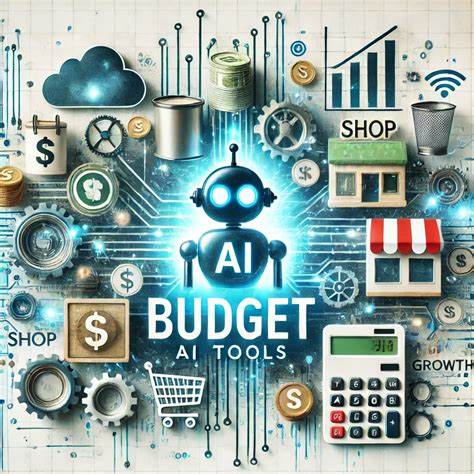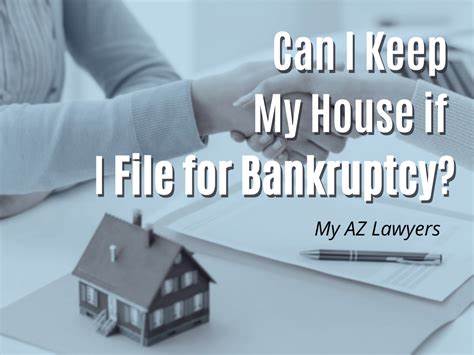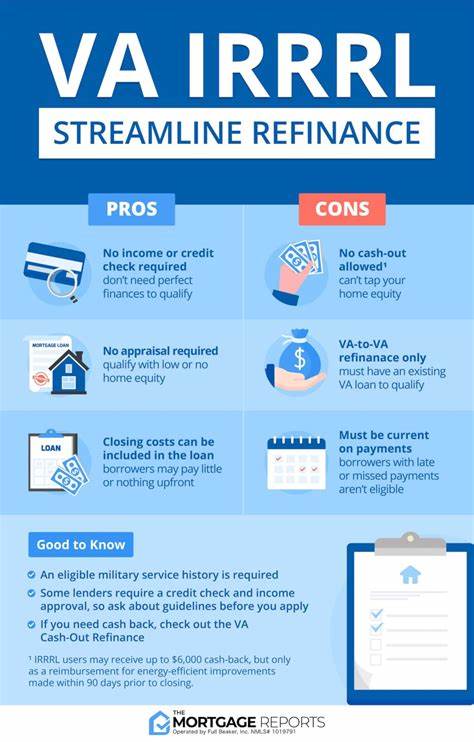19世纪的海洋航运业蓬勃发展,但与此同时,一种令人震惊且带有暴力色彩的现象悄然滋生并广泛存在,那就是“上海招工”(Shanghaiing)。这一术语源自于航海界,用来描述将人以欺骗、威胁甚至暴力的方式强行招募为船员的行为。上海招工不仅反映了当时海运业劳动力短缺的严峻现实,也折射出社会法制的不完善以及劳动者权益难以保障的困境。上海招工的历史起伏和其深远影响,成为研究海洋历史和工人权益的重要切入点。 上海招工最早起源于19世纪中叶,那个时代全球航海业进入鼎盛阶段,尤其是在欧美和北美的港口城市,商船与捕鲸船数量激增,然而合格且愿意出海的水手却严重短缺。加之当时法律对船员的限制极为严苛,一旦签约便不得随意离船,极大地加剧了船员的脆弱境地。
上海招工者,也称“招工中间人”或“骗工者”,通常在港口的酒馆、旅店以及码头附近活动,故意利用醉酒、药物或直接施暴手段使目标水手失去反抗能力,然后伪造签约,强迫其上船。此举使得船东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迫切需要的劳动力,尤其是在美西海岸如旧金山、波特兰及东海岸城市如纽约、波士顿等地尤为普遍。 “上海”这一词汇本身,反映了被强行送往远东,尤其是中国上海港的水手经历,因此“上海”一词逐渐演变为被强迫或欺骗的代名词。虽然这一现象得名于中国的上海,但实际上涉事多数为美国和英国的港口城市。这段历史的核心,不仅是对水手群体的剥夺与凌辱,更是海运经济体制和劳动法律滞后的直接结果。 上海招工盛行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航运业需求旺盛,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淘金热期间,船只频繁往返,急需经验丰富且体力充沛的水手来保证航行安全。大量船员因不满恶劣的工作环境及长期的孤立状态而选择逃离,导致劳动力极度紧缺。其次,法律限制船员中途脱离合同,使得水手在签约后即陷入法理上的束缚,难以抵抗招工者的压迫。第三,负责招募船员的中间人,即“招工头”往往“按人头”计酬,他们既是体制内的一环,又通过欺骗手段攫取巨额利益,被称为“血钱”。这导致招工头极力寻求各种手段扩大招募数量,甚至不惜使用暴力和造假伎俩。上海招工由此形成一种黑暗但有利润驱动的地下产业链。
上海招工的实施手段多样,最直接粗暴的方式便是将人灌醉或下药,直至昏迷;随后伪造其签名将其纳入船员名单,船主支付“血钱”给招工头,而被招徕水手往往处于无力反抗的境地。然而,也有更隐蔽的方式,例如通过搭伙供应高价船员用品、先发放工资预付款等金融手段控制水手经济,迫使其不得不上船。无论何种手段,其核心均是对个人自由和意愿的侵犯。在这种恶劣环境下,水手不仅要面对艰苦的海上劳作,也承受着精神和身体上的双重摧残。 随着19世纪晚期以来社会舆论对这一现象的逐步关注,以及工人运动的兴起,上海招工逐渐被视为剥削和非法行为。多个立法行动相继出台以规范航海劳动环境和保护水手权益。
美国于1872年通过《航运委员会法》,规定船员必须在联邦航运委员面前签约,防止招工头恶劣行为。1884年的《丁格利法》则禁止水手提前领取工资,减少招工头通过金融控制获利。尽管如此,招工者利用法律漏洞继续牟利的现象并未完全消除。真正压垮上海招工的,是随时间推移蒸汽机船的普及和自动化程度的提升,降低了对大量低技能水手的需求。1915年,美国颁布《海员法案》,正式将强迫招工定为联邦刑事犯罪,标志着这一不法行为的终结。 上海招工不仅仅是一段航海史上的黑暗章节,也深刻影响了港口城市的社会结构与文化。
在旧金山、波特兰等地,围绕强迫招工的犯罪网络与政治势力纷纷滋生,腐败现象层出不穷。相关人士如“上海凯利”等人物,成为传奇也成为罪恶的象征。港口的“招工旅馆”成为社会阴影,船员们的处境多被边缘化和忽视。多部文学作品、电影及戏剧亦以这一题材为素材,反映当时社会的动荡和无奈。 同时,上海招工也揭示了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艰难历程。水手群体作为最早被现代劳动法关注的群体之一,其权益争取过程反映了司法体系对强制劳动问题的渐进认识。
从强迫签约、剥削至制度建设的转变,见证了工业文明进步与人权观念提升的历史轨迹。现今,许多国家的海事法律中,对海员自由、强迫劳动有绕不开的规范,上海招工的历史教训依然警示着全球航运业。 纵观上海招工的历史,其背后是经济利益驱动下的劳动力剥削,其表面是海运业的需求和劳动保障的缺失。它既是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全球化经济发展的副产物,也反映了弱势群体在社会结构中所处的脆弱地位。尽管这种现象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对现代劳工权益保护制度的建立,以及对强迫劳动的认知仍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上海招工提醒我们,经济发展不可忽视人的基本权利,不论是在陆地还是海洋上,对自由的保护都是文明社会的基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