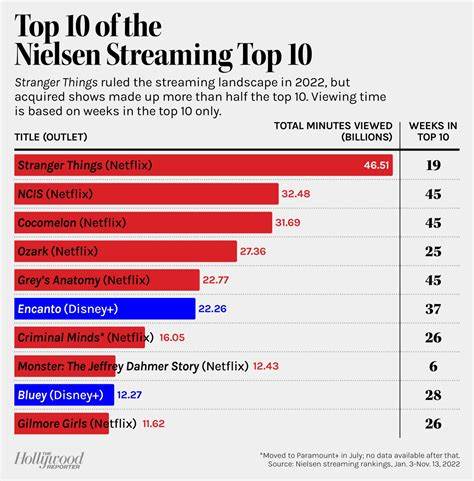公海,指的是国际水域,占据了全球海洋的61%,覆盖地球表面43%的面积,是地球上体积最大的生物圈,也是维持地球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尽管公海在全球生态系统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其保护现状却极为不足,迄今为止仅有不到1%的公海区域获得保护。随着人类对海洋资源的不断开发,公海的生态环境和全球气候系统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永久保护公海,禁止一切形式的资源开采,已成为保护地球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公海自十七世纪开始被人类开发利用,最初主要是以捕鲸为主,到了二十世纪中期,捕捞鱼类、鲨鱼和鱿鱼的活动大幅增加。这种长时间的过度捕捞不仅导致海洋生物数量锐减,甚至使一些物种濒临灭绝。
同时,气候变化加剧了公海生态系统的压力,海洋变暖、营养盐和氧气含量下降,进一步降低了海洋生物的生产力。近年来,更深海域的捕捞和海底采矿的兴起,可能对海底生态系统和碳循环造成无法逆转的损害。公海作为地球最大的碳汇,其海洋生态系统通过“生物泵”和“营养泵”两大机制对全球碳循环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生物泵是指许多生活在中深层光照不足区域的鱼类和无脊椎动物白天潜入深海,排泄含碳废物,夜晚返回浅层水域,帮助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通过生物活动沉积到深海中。如果没有这一机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可能高出200 ppm,全球气温也可能比工业革命前升高3摄氏度以上。营养泵则通过海洋生物的进食和移动,促进深层和浅层水域之间养分的循环,维持表层海洋的生命活动和生产力。
这两种机制的正常运作依赖丰富的海洋生物种群,而过度捕捞正严重破坏这些基础。长期以来,人类对全球海洋,尤其是公海的捕捞活动不断加强。政府补贴和技术进步推动了高海洋捕捞量,但这也带来了严重的生态后果。许多目标捕捞物种数量锐减,不少海鸟、海龟、鲨鱼等的非目标捕杀数量也居高不下,生态链受到破坏。使用鱼聚设备(如卫星追踪的漂浮鱼聚装置)等现代捕捞技术虽然提高了捕捞效率,但也导致大量非目标物种死亡,加剧了生态风险。公海渔业的经济效益并不乐观,捕捞收益往往依赖巨额的政府补贴,这种依赖不仅耗费了公共资源,也导致渔业的长期不可持续发展。
经济上,全球高海洋渔获量仅占全球总渔获量的6%以下,其中80%的渔获来自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层面,高海洋捕捞对大多数贫困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没有直接贡献。多国研究指出,关闭公海捕捞不仅可以让濒危物种恢复数量,还能将渔业资源引导回国境海域,在更为有效的管理框架下实现可持续利用。除了捕捞,深海矿产资源的开发也成为威胁公海生态的重大因素。尽管商业性开采尚未启动,公海海底已有30多份勘探合同,这一领域的监管缺乏透明度和问责机制,深海矿产开采可能破坏海底生物栖息地,释放数千年来沉积的碳,有加剧气候变化的潜在风险。反对深海采矿的声音日益增多,许多科学家和国家呼吁暂停该行业的发展,强调应遵循预防原则,保护海洋生态完整性。保护公海的挑战在于缺少强有力的国际治理机制。
尽管2023年联合国通过了高海洋条约,意在填补这一治理空白,推进国际水域的保护区建设,但条约生效前还需至少60个国家批准,目前仅有不到一半国家完成了批准程序。条约的实施也面临数据不足、多边合作难题和责任划分不清等问题。气候危机和生物多样性危机的紧迫性已不容等待。海洋生态系统一旦遭到破坏,恢复将耗费数百年甚至千年时间。采纳永久性的公海保护方案不仅是避免生态灾难的关键,也是保障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永久禁止公海中的捕捞、深海采矿和石油天然气开采,能够促进海洋生物多样性的恢复,增强全球碳汇功能,从而助力抑制气候变暖。
在保护措施实施后,渔业活动可以更集中于国家管辖的海域,在更有效的管理和监控下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促进渔业的长期健康发展。同时,保护公海不会阻碍国际航运、科学研究和非提取性利用,如生物探测等,为科学界和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研究与发展空间。历史上,人类在1950年代联合保护南极大陆的成功经验,证明跨国合作保护地球关键区域是完全可能的。公海保护的倡议同样需要全球共同努力与支持,以确保人类和地球生态系统的未来免受破坏。面对既有的科学证据和迫切的行动需求,国际社会必须加快批准高海洋条约的进程,构建强效的海洋治理机制,加强研究数据的支持和监管合作,推动实行永久性的全面保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守护地球上最大的碳汇,保障海洋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威胁,真正实现海洋资源的持续利用和公平分配。
保护公海不仅是环境保护的诉求,更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公海的未来需要我们今天共同作出科学、理性和负责任的决策,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开创持续繁荣的蓝色地球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