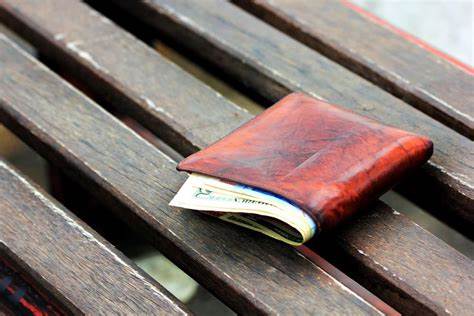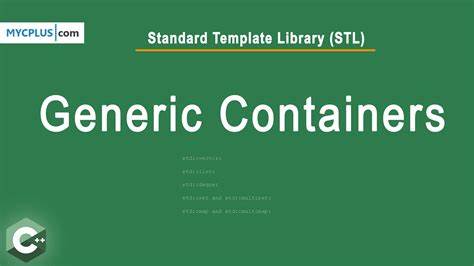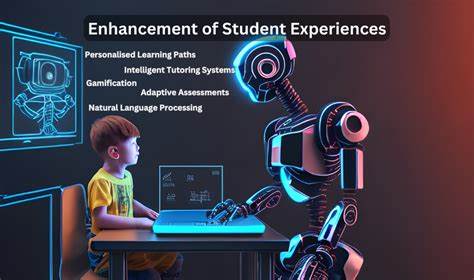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的崛起,科技与政治的结合引发了关于“科技法西斯主义”的严肃讨论。2025年社会社会主义大会成为了分析这一现象的重要平台,在这里,思想者们警醒于硅谷科技教派对社会的深刻影响及其与资本统治的紧密联盟。科技法西斯主义不仅仅是科技的独裁,更是一种以科技为核心、深刻渗透社会肌理的极权形态。社会上的许多科技狂热支持者将人类看作仅仅是人工智能的生物启动器,蔑视现实中人类的痛苦和情感,将共情视为文明发展的障碍,甚至是一种“自杀性”的行为。这种观点将人类未来的命运寄托给冷冰冰的技术力量,掩盖了背后错综复杂的资本主义利益驱动和阶级压迫。 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及其相关技术对社会的冲击尤为明显。
无论是因为自动化导致的就业岗位流失,还是环境破坏引发的生态危机,科技产品对普通人生活的侵蚀日益加剧。更为严重的是,人工智能等技术正在重塑人类的交往方式,冷却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情感联系。以聊天机器人为例,其不仅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更让许多弱势群体陷入了虚幻的慰藉之中。这种人工陪伴的虚拟交往虽然似乎带来了精神上的安抚,却往往制造了心理依赖,甚至滋生了孤立与心理疾病。人们逐渐丧失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把自己的思想与感受交付给了机械式的自动补全与算法推荐,这种现象正是科技法西斯主义在精神领域的深远体现。 此外,算法治理与数字平台的统治方式也将暴力与控制机制进行了系统化和自动化。
曾经依赖人类执行的行政暴力,如社会福利审批、危机应对等,如今被冷酷的算法替代。虽然算法表面上以“无偏见”“公平”为幌子实则反映财富与权力的优先级,导致弱势群体被机械地边缘化甚至抛弃。大科技公司同时通过制造技术依赖,牢牢掌控公众与政府的认知与行动动力,使得反抗变得更加困难,而监管与监督的空间被逐步压缩。科技不再是中立的工具,而成了资本主义极权的延伸,演化成由科技大亨主导的企业封建王国。 这其中,与基督教民族主义的结合形成了令人警惕的“末世法西斯主义”。一些科技精英与基督教民族主义势力的联合,既借助了传统宗教的扩张性幻想,也激发了基于毁灭性的政治图景。
这一交织体不仅在政治上为极右势力提供了助力,更在文化和精神层面强化了排他、偏执与末世论,使得科技何去何从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面对科技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挑战,社会主义者、劳工组织和文化抗争者提出了多重应对策略。首先,强化工会力量至关重要。技术并非不可战胜,工人的专业技能依旧是经济运转的根基。通过建立新一轮的“卢德运动”,工人可以反抗技术异化,维护劳动尊严,争取对技术发展的主导权。同时,支持全球南方被剥削的AI训练工人以及受到产业污染影响的社区,成为国际团结和社会正义的关键一环。
其次,文化和社会层面的反抗同样不可或缺。在数字化异化日益严重的时代,回归线下交流与真实社会关系的建设,能够促进人们的情感联结与批判意识。像黑人文化杂志集市、囚犯书友会等草根文化活动,不仅提供了知识传播的空间,也成为抵抗高科技监控与异化的文化堡垒。此外,精神上的陪伴和社区互助,在面对孤独和系统性危机时显得尤为重要。 最为根本的,是重新赋予社会运动以人文精神和互助的力量。许多人面临孤独、精神危机和社会疏离,右翼势力善于利用这些脆弱点,推动宗教狂热和极端主义的扩散。
反观左翼运动,需要在坚持理想的同时,为人们提供鼓励理解和身份承认的平台,通过互助小组和学习圈层,增强集体的抗争力和心理支持,从而建立一种超越生产力框架的生命价值体系。 总之,科技法西斯主义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在新技术驱动下的异化和统治形态。它通过破坏人与人之间的真实连接,削弱社会的批判力量,从而巩固极少数人的权力。面对这一极权威胁,唯有通过强化工人阶级力量、文化反抗和精神互助,才能构筑有效的抵御防线。社会主义2025会议的讨论为我们指明了反抗的方向:坚持人的价值,重建真实关系,拒绝被机器简化和同化,因而才能在这场科技与资本的博弈中,赢得属于全人类的未来。这场斗争不仅关乎技术,更关乎人性与自由的本质,是当代社会必须深刻回应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