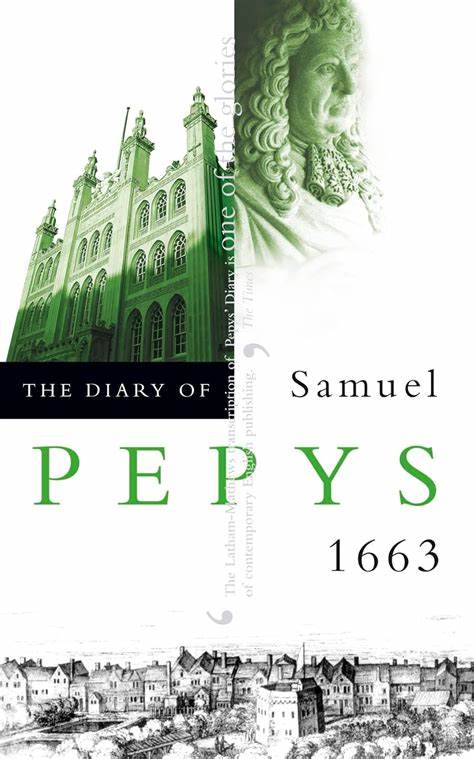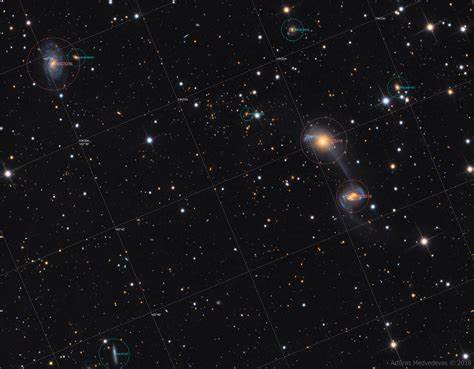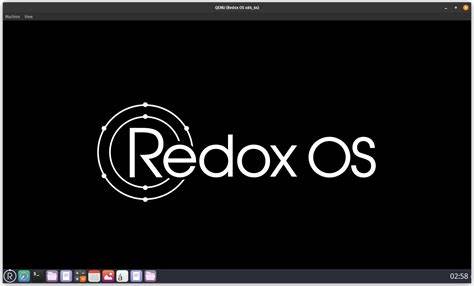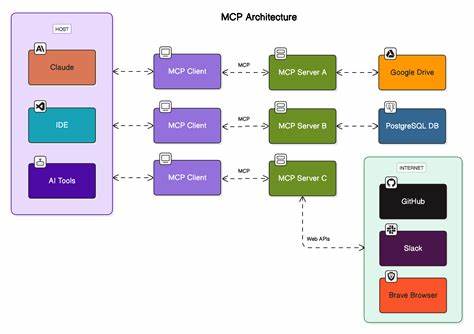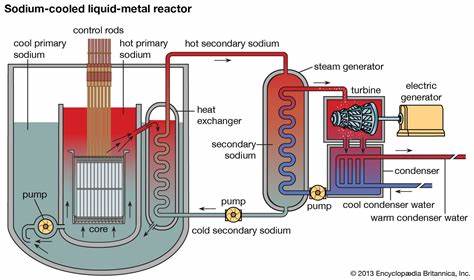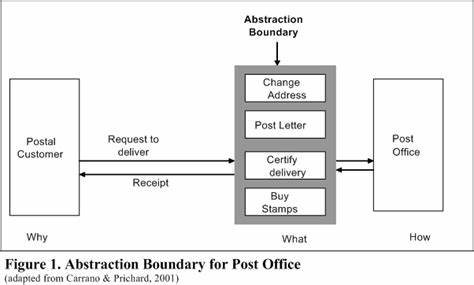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是17世纪英国历史与社会生活的生动记录。佩皮斯本人是海军官员,生活在1660年代的伦敦,他以极富个人色彩的视角记录了英国历史上多个重大事件,比如伦敦大火与瘟疫。然而,尽管这部日记极具历史和文学价值,佩皮斯在生前却极力隐瞒其存在。多年来,如何将这部充满私密细节的文稿转化为公开出版的书籍,一直是学界与出版界的一个传奇故事。佩皮斯日记首次出版,距他去世已有约120年之久,这段时间内,日记被谨慎保存,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接触到它。佩皮斯在去世时将包含日记的藏书遗赠给剑桥大学玛格达琳学院,限定只有学院的院长能够借阅并保管这些手稿。
日记以托马斯·谢尔顿的速记法写成,内容繁复难懂,外人难以破解。正是这种写作方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护了日记内容的私密性。19世纪初,约翰·埃夫林的日记出版成功,激起了人们对佩皮斯日记的兴趣。尽管如此,速记法的秘密尚未被普遍识别,佩皮斯日记依然是谜一般的文本。剑桥玛格达琳学院当时的院长乔治·内维尔,将日记的第一卷秘密送给了伯爵格伦维尔去判断其出版价值。格伦维尔费尽心思破解开头部分速记,判断这部日记可以成为《埃夫林日记》的绝佳补充。
然而,这批行为实则突破了佩皮斯遗嘱中严格的藏书保管条款,因此格伦维尔极力保持自身身份隐秘,避免学院失去藏书权。随后,一名剑桥学生约翰·史密斯被雇佣负责把速记内容转录成通俗易懂的英文。这项工作极其艰辛,历时三年,劳累非凡。史密斯自称是这部日记的“译码者”,试图以此展现自己对这一复杂速记系统的独特掌握。然而,后来关于到底是谁首次真正“破解”速记体系的争议不断,格伦维尔家族成员试图声称功劳归属于他们。事实上,史密斯在转录工作中,得到了佩皮斯藏书中速记手册的帮助,从而成功辨认并应用了谢尔顿的速记法。
为了维护独家优势,史密斯并未公开这一事实。首次出版版本由内维尔的兄弟布雷布鲁克勋爵担任编辑。布雷布鲁克在编辑中采取了删减策略,只公开了日记内容的约四分之一。删减的原因是佩皮斯日记中涵盖过于琐碎的日常事件以及部分不适合公开的细节。特别是涉及佩皮斯个人受贿和私生活的敏感内容被全面剔除,编辑试图维护佩皮斯的名誉,也保护自己兄弟学院的声誉。然而,出版商亨利·考尔本并不十分符合这类保守处理的理念。
他以推销手段强硬著称,借助报纸和宣传制造话题与猜测,吸引公众关注。考尔本安排的报纸评论暗示日记中被删节的内容异常精彩且有争议,这种“欲盖弥彰”的营销策略迅速提升了该书的知名度和销量。佩皮斯日记在被秘密转录、筛选和出版过程中,各方都借助智慧和策略,从隐秘的手稿变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著作。它一方面被称赞为极其诚实的生活记录,另一方面又通过隐蔽的“巧手”保持了适当的“体面”,以适应19世纪的出版规范与读者心理。这场出版风云不仅体现了对文化遗产的珍视,更反映了出版世界的复杂博弈。佩皮斯本人尽管生前受限于当时社会的压力,仍留下了能够穿越百年光阴的珍贵笔触。
几经波折,日记不仅为后人了解17世纪的英国社会风貌提供了独特视角,还成为文学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基石。如今,研究佩皮斯日记不仅关乎内容本身,更涉及版权史、出版伦理以及文化传承的多重维度。佩皮斯日记的出版故事是历史与文学、隐私与公共、秘密与揭秘之间复杂关系的典范。理解这些曲折的出版历程,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这部跨越时代的文学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