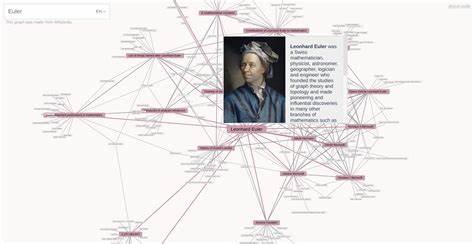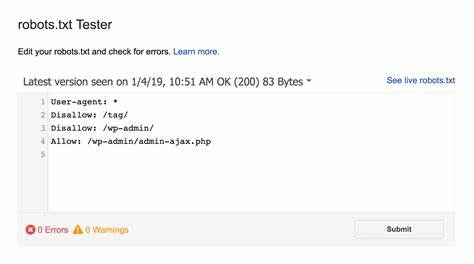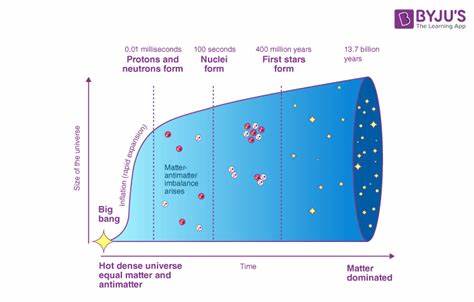近年来,围绕文学衰退的讨论在文化领域引发了热烈争议。作为社会观察者和知识分子,David Brooks在其文章《当小说重要时》里提出,文学作品逐渐失去影响力,而这一变化背后,则与社会政治氛围及文化风向息息相关。然而,作家和评论家林肯·米歇尔针对这类观点进行了尖锐反驳,认为很多结论建立在事实错误及过度简单化的假设之上。通过对出版行业和读者市场的深入分析,米歇尔展示了文学衰退论调中的认知失调与误读,带来了更为务实和多维的洞察。要理解当前文学的现状,必须首先破解“文学小说”这一概念的历史与市场背景。实际上,“文学小说”与“文学小说衰退”的讨论不过是1980年代以来才逐渐形成的文化标签。
此前,小说基本上包括通俗小说、科幻、爱情、惊悚等类型,而所谓“文学小说”是用以划分那些“非商业性”甚至带有挑战性的作品。随着市场的成熟,这一定义不断演变,甚至出现将畅销作者如德莉亚·欧文斯、E.L.詹姆斯等也归入“文学小说”的现象。很多所谓文学衰退的论述,在语义上都是模糊且自相矛盾的,因为谈论“衰退”之前,文学及其分类的界限就已模糊不清。除了定义上的混乱,米歇尔指出,许多文化评论者陷入了认知失调的陷阱,他们一方面相信作品的流行即是文学价值的体现,另一方面又因为流行作品不符合自己喜欢的品味而否认这种流行的正当性,从而用“左翼审查”“文化压力”等阴谋论来解释市场变化。他们忽略了一个关键现实: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时代,传统的“守门人”角色已不再主导市场。出版社、编辑、评论家曾经在过去数十年对大众文学的传播起到强大影响,但如今TikTok、豆瓣、甚至自助出版的读者和写作者网络,才是真正决定书籍命运的关键。
社交平台驱动的病毒式传播现象,带来了新的畅销作者,甚至令传统文学巨匠的作品在发行多年后成为爆款。显然,读者的需求和喜好在发生转变,且这种转变不再只受官方或媒体的引导。米歇尔进一步指出,现代出版业从根本上是一个由利润驱动的庞大产业。五大出版社包括哈珀柯林斯、哈切特、企鹅兰登、Simon & Schuster和麦克米伦,它们都属于更大规模的跨国集团。出版社为了适应市场变化,设立了涵盖奇幻、浪漫、非小说、青少年文学、自助等多样化的子部门,尝试覆盖各种读者群体和市场细分。这种“多元战略”意味着,即便是反“酷儿”或“反觉醒”题材也有自己的市场尝试机会。
行业采取“试验—检验”策略,投入巨资寻求下一部爆款,而不是执着于传统的“高雅文学”标准。除了市场机制的变化,文化领域整体“高雅文化”地位的下降也是文学话题中的重要背景。电影、音乐、美术等领域都经历了类似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娱乐的转变。电影票房被超级英雄大片和重启作品垄断,音乐排行榜频繁由流行与说唱占据。文学作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自然免不了受到这一趋势影响。将文学视为孤立的现象,无视整个文化生态的变迁,并不能有效解释现状。
对读者个人层面而言,虽然批评家们时常表达对当代文学“晦涩”和“乏味”的不满,但像乔纳森·弗兰岑、欧申·武昂等作家仍拥有百万销量和广泛读者群,说明“文学读者”这个群体及其需求依然存在且不容小觑。事实上,对于“严肃文学”爱好者而言,真正的挑战是如何在庞大且碎片化的市场中发现并传播优质作品。不可否认的是,发现好书的难度正在上升,分发渠道的多样化意味着读者需要更多渠道和资源去主动寻找,而非依赖传统的排行榜、媒体评论或者文学奖项。米歇尔强调,文学现状的关键其实是“发现难”,而非“不存在好的文学作品”。他列举了大量依然在创作不同风格和主题高质量作品的作家名单,提示广大读者应跳出畅销书排行榜的局限,拓宽视野,从独立出版、翻译作品、网络文学乃至社交平台中寻找令自己共鸣的人文价值。出版统计数据显示,美国每年出版超过三百万册图书,毫无疑问,存在满足各种兴趣的精品。
流行文化的优势,市场需求的多样,技术传播的便捷,是文学生态极为丰富和复杂的表现。总结而言,文学的变迁是一面折射文化、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镜子。布鲁克斯等人的文学衰退论往往未能洞察其中的多层次现实,不仅曲解了数据,也忽略了文化整体生态的深刻演变。相反,从市场机制、读者行为乃至跨媒介文化趋势出发,能更科学地把握文学的现状与未来。对广大作家和读者而言,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现实中的文学,既未消亡,也未陷入单一困境,只是呈现出更加多样和分散的形态,需要我们用更开放和理性的态度去阅读、交流和支持。
现在,当下依然有许多光彩夺目的书籍和作者等待被发现。与其怀旧地怨叹“文学没落”,不如积极寻找、传播和推动。当文学作品跨越媒介,回归到与读者的真实连接,或许就是新一轮文化繁荣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