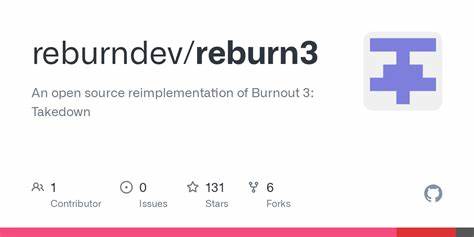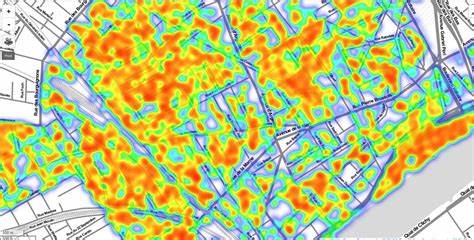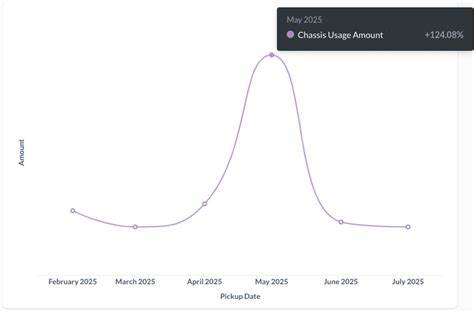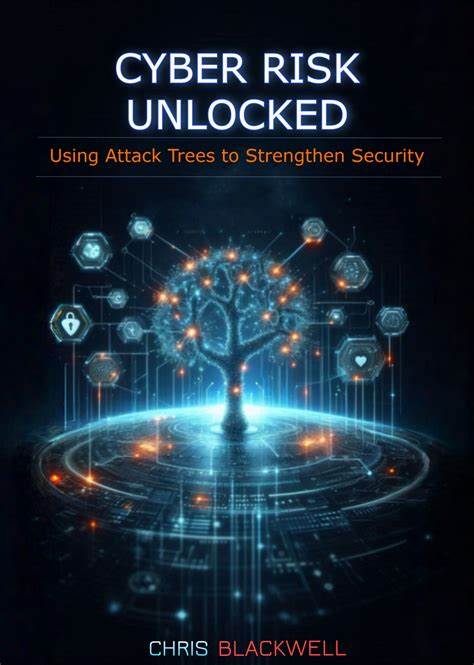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值越战、民权运动以及社会动荡时期,地下激进运动席卷都市,爆发了大规模的政治暴力行动。在这个时期的历史画卷中,"愤怒的日子"(Days of Rage)成为了激进左翼暴力抵抗的代名词,伴随着炸弹袭击、银行抢劫和武装抗争,这段历史却被现代社会遗忘甚至选择性忽视。理解那一时期的事件不仅有助于解读美国的政治历史,也为当代可能再现的政治暴力形态提供警示和借鉴。 1970年代的地下激进运动绝非边缘小众,它聚集了上百名激进分子组成的城市游击队,针对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国会大厦、法庭、企业及餐馆在内的各类机构展开一系列爆炸及袭击行动。这些行径背后,是一群深信革命迫在眉睫、认为暴力手段能加速社会变革的激进理想主义者。令人惊讶的是,尽管活动范围广泛且影响极大,这段历史却早已被公众和主流媒体淡忘,许多关键细节鲜为人知。
这场运动的起点可追溯至校园,最初的抗议和暴力行为大多发生在大学校园内,随后逐渐转向城市外围。著名的激进人物桑姆·梅尔维尔(Sam Melville)受加拿大学运分裂派的革命战术影响,开始了针对企业和银行的爆炸袭击。这种以炸弹抗议为核心形式的暴力行动,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被许多激进团体效仿,而由此催生的城市游击队式暴力被称为"炸弹时代"。 但70年代地下运动的重点并非单纯抗议越战,其核心关切更多聚焦于黑人权利和社会正义问题。黑人激进分子如罗伯特·威廉姆斯、马尔科姆·X、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休·拉普·布朗和休伊·牛顿等人,推进了激进的抵抗理念,而埃尔德里奇·克利弗(Eldridge Cleaver)则以其激进且极端的观点迅速走红,他不仅是知名作家,更以其宣扬黑人民族抵抗的暴力手段而闻名,引发了白人左翼对黑人民权运动领导的崇拜和矛盾心态。 "气象人"(Weatherman)组织的兴起,是70年代激进学生运动的高潮之一。
作为"民主学生组织"(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的激进分支,气象人致力于在城市环境中建立游击力量,信仰菲德尔·卡斯特罗及切·格瓦拉的"聚焦理论",认为小规模游击战士能够引发全面革命。 尽管他们策划了多起爆炸,包括针对警察局和政府建筑,但也因误操作而引发多起事故,甚至炸死自家成员。随着内部矛盾、社会支持度下降和警方高压,气象人逐渐转入地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气象人并非纯粹的暴力团体,他们强调所谓的"直接行动"和"多样化战术",在社会运动中寻找合法与非法的边缘地带。 70年代另一股鲜为人知的激进力量是由黑人激进分支衍生而成的黑人解放军(Black Liberation Army,BLA),他们是黑豹党的分裂派,以针对警察的武装袭击为主要行动。BLA频繁通过抢劫筹措经费,激进又高效的行动导致纽约、芝加哥、新奥尔良等大城市警察遭受数起致命袭击。
在BLA的成员中,乔安妮·切西马德(Assata Shakur)以其传奇经历成为黑人激进主义的象征,同时也显示出激进暴力内部的复杂现实。 与此相辉映的是解放军与女性激进组织以及白人马克思主义者(如五月十九共产党组织)的联手,他们合力推动了"家庭"(The Family)这一激进集体的形成,参与银行抢劫、武装越狱等极端事件,彰显了多种族、多阶层激进元素的结合。 洛杉矶的象征性团体同样引人注目,象征解构和血腥的共生解放军(Symbionese Liberation Army,SLA)以绑架豪门千金帕蒂·赫斯特(Patty Hearst)事件名震一时。SLA宣扬"消灭寄生的法西斯昆虫",一方面进行暴力恐怖行动,另一方面试图借助媒体博取关注,但内部腐败和警方围剿使其迅速走向瓦解。 另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是激进组织与主流机构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波多黎各独立运动中,激进恐怖组织联盟解放民族阵线(FALN)甚少为人知的幕后支持者竟是美国圣公会教会。
他们不仅为FALN成员提供职位和掩护,还通过慈善机构为其提供资金。这种"制度寄生"模式,是70年代美国激进运动能持续长久的重要原因,也是当代政治暴力难以根除的制度根基。 70年代地下激进运动的"遗忘"与现今公众认知的脱节,部分缘于媒体和政治对激进左翼的容忍和包容。许多激进分子,即使涉及炸弹袭击、警察杀戮等严重犯罪,最终也未受到严厉处罚,反而有机会重返社会,获得教育和职业机会。反观极右派激进者,束手就擒且难以获赦免。 这种不对称的司法与社会态度造成了激进左翼势力的深厚根基,令他们不仅在当下具备组织和动员能力,也能在未来形成持续影响力。
今日的美国面临新一轮政治暴力风险,这一点值得深刻反思。 从1970年代激进左翼运动中的多样化战术和复杂结构可见,未来的政治暴力形态或许会呈现出分散而多元的特点。激进左派拥有较为完善的组织体系、法律支援和社会网络,这使得有计划的暴力行动更易展开且更具持久性。相反,极右派往往依赖单一行动者,缺乏系统化支持,难以对社会秩序造成大规模冲击。 另一方面,激进左翼的"制度寄生"和对"震慑者"或激进分子的长期支持,也使得他们能制造出更具战略价值和社会影响的政治运动。这种组织能力和资源优势,可能在未来的社会对立中发挥极大作用,尤其当经济社会压力剧增,政治极化加剧时。
然而,我们也必须看到,尽管激烈的左翼运动能力更强,但这种持续的暴力和分裂同样可能造成社会长期的撕裂,令国家陷入"冷战"式的对立状态,逐步滑向全面内战的边缘。历史已多次证明,政治暴力不以意志为转移,它的后果极为严重且难以收拾。 因此回溯"愤怒的日子"这段鲜为人知但影响深远的历史,有助于当代社会更清醒地认识到政治暴力的根源及其复杂的社会网络与制度基础。同时,也警示当下乃至未来的政策制定者和公众,必须正视政治分裂的深层次矛盾,在防范暴力激化的同时,努力寻找和平共处与社会整合的可行路径。 总结而言,1970年代的美国地下激进运动,"愤怒的日子"不仅是一段充满暴力和理想交织的历史,更是当代政治暴力形态的实验场。它揭示了激进运动的复杂面貌、多渠道支持和强大组织能力,同时也暴露出社会容忍度和司法执行上的不平衡。
理解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洞察当前和未来可能重演的政治暴力模式,提升防范能力,保护社会稳定与民主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