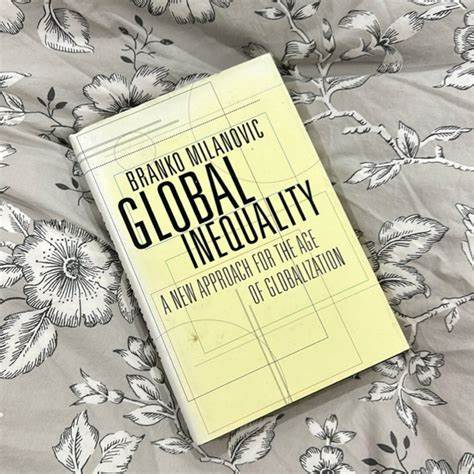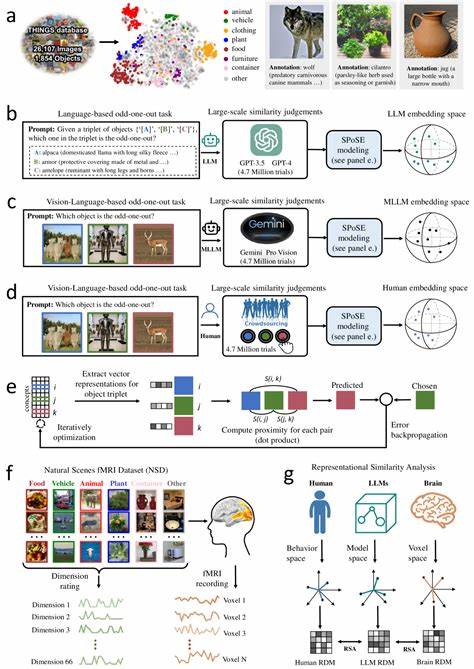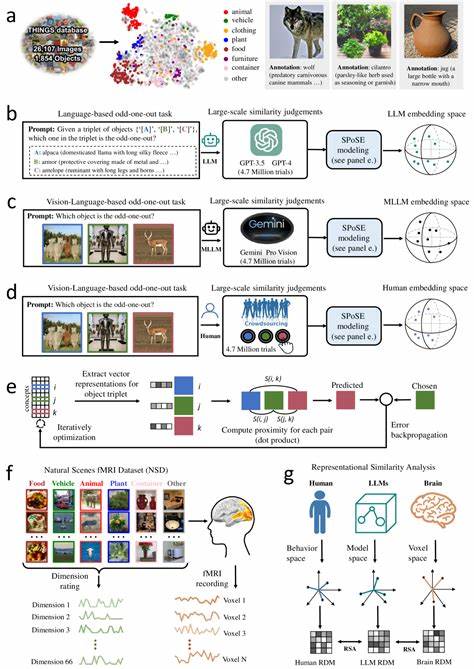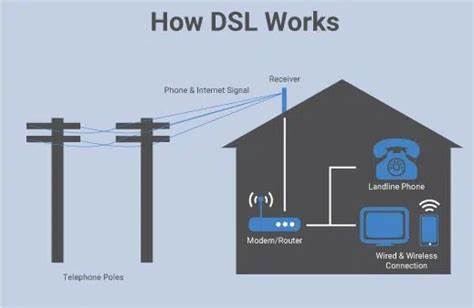全球不平等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学讨论中的核心议题之一。作为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以其对全球收入分布的系统研究而闻名,尤其是通过他的“象形曲线”揭示了全球收入增长的复杂格局。理解全球不平等,不仅需要对各国国内的不平等进行分析,更要从全球公民的视角,考量贫富差距的跨国维度。米拉诺维奇对此提出独到见解,深刻揭示了数据采集的挑战、全球化的双刃剑效应以及不平等背后的哲学与社会政治问题。 在谈论全球不平等时,米拉诺维奇采用的核心概念是“世界公民间的不平等”。这一视角超越传统的国家界限,将全世界范围内的收入分配整体纳入考量。
技术层面来看,将各国分散的调查数据统一转换为可比的购买力平价(PPP)数据,是衡量全球不平等最基础却最具挑战的环节。尤其是在非洲等数据缺乏的地区,这一工作更是现实难题。米拉诺维奇指出,即便是在近年,非洲部分国家的收入调查依然稀缺,这直接影响到全球不平等测量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从全球视角审视不平等,最令人瞩目的是米拉诺维奇著名的“象形曲线”。这条曲线描绘了从1988年至2008年全球人口在收入增长方面的表现,呈现出独特的非单调形式,如同一头象的轮廓。曲线显示处于全球中间阶层——主要是中国及印度等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经历了显著财富增长,而全球富裕的顶端1%同样大幅受益,形成了曲线的“象鼻”和“象耳”部分。
相反,许多传统发达国家的中低收入群体却未能分享同样的增长机遇,造成了曲线中间的下陷部分。这种结构性的收入增长不均,折射出全球化进程中的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分化。 米拉诺维奇对于全球不平等趋势的判断也颇具启发性。他强调,尽管许多发达国家内部的不平等在过去几十年有所上升,但全球不平等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是由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的快速经济增长带来的均衡效应。换言之,国别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在全球范围内达成了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然而,米拉诺维奇同时指出,这种趋势并不意味着不平等问题得到解决,尤其是在内部阶层差异日益突出的发达国家中,社会经济的裂痕依然明显。
除了数据和趋势的分析,米拉诺维奇还从哲学和政治经济的角度探讨全球不平等。这其中涉及到“机会平等”的全球适用性问题。例如,一个赞比亚卡车司机与美国卡车司机在工作性质和付出努力上并无显著区别,却面临着巨大的收入差距,这引发了关于公平与正义的深刻反思。米拉诺维奇提出,全球层面的收入差异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伦理和政治体制的挑战,触及到国籍、主权与全球公民身份等复杂因素。他提到,很多政治哲学家对此高度关注,探讨如何实现跨国界的公平,却发现这在现实中极难实施。 谈及全球化与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米拉诺维奇将“象形曲线”看作是“超级全球化”时代的产物。
这个时代起始于冷战结束蓬勃发展的全球商品与资本流动,极大推动了新兴经济体的成长,并拉动了全球经济的整体均衡改善。然而,金融危机与地缘政治冲突等因素在2008年后逐步阻碍了这一趋势,顶端财富的快速积聚也有所放缓。他强调,尽管超级全球化的光环渐退,但中产阶级的全球化红利在某些地区依然延续,尤其在中国和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城市群体中表现明显。 米拉诺维奇还在其著作中回顾了历代经济学家对于不平等的思考,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再到马克思与库兹涅茨,每一位经济思想家的观点都影响了现代对不平等问题的理解。特别是他指出,斯密对当时资本家的批判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理念大相径庭,揭示了资本主义内部利益冲突的复杂性。李嘉图则凸显了不同阶级间的收入分配及其对经济增长不可分割的影响。
米拉诺维奇强调,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转向使收入分配问题在理论上被边缘化,但现实的财富鸿沟却从未消失。 面对当今激烈的全球不平等问题,米拉诺维奇的研究提供了具有指引意义的分析框架。他提醒人们,出生国家对个人收入的影响巨大,是决定个体经济命运的关键因素——据他的研究,出生国家和家庭社会地位变量可以解释全球90%的收入差异。这一事实挑战了传统的“机会均等”理念,提醒我们思考全球治理与跨境社会政策的新可能性。 总之,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以多维度、多层次的视角,结合严谨的数据分析与深刻的理论探索,揭示了全球不平等的复杂面貌。他的研究不仅帮助我们理解当前全球经济不平等的现实,更启发我们反思如何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经济秩序。
在全球化遇到挑战、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米拉诺维奇的洞见为政策制定者、学者和公众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思考路径。未来,只有以全球公民的视角,超越国界的限制,才能真正应对这一关系所有人福祉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