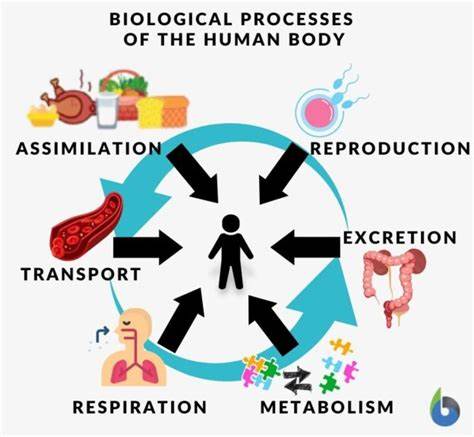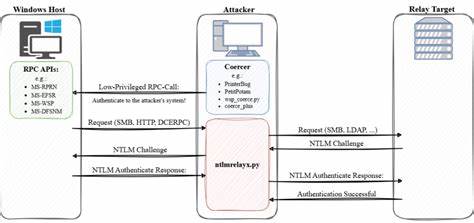生命的定义一直是科学界和哲学界共同探讨的难题。传统的生命观大多基于地球上的生物特征,如细胞结构、自我复制以及基于碳的化学组成等。然而,这种基于地球生命形态的定义多少带有一定局限性,使我们在探索宇宙其他角落的生命时陷入“地球中心论”的窠臼。随着科学不断进步,我们是否需要用一个更为普适且根植于物理学基础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生命的本质?生命与第二类热力学定律的冲突曾困扰无数科学家。热力学的第二定律陈述自然系统向混乱和熵增方向发展,似乎无法解释生命是如何在无序中创造和维持复杂有序结构的。从细胞到生态系统,再到城市和太空飞船,生命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复杂性和创造力,令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生命在物理世界中的角色与意义。
近期,Sara Walker 所著《未知的生命》一书提出了一个颇具启发性的观点,即生命应该被视为一种物理过程,一个不断生成并维持“统计上极不可能自发组合”的复杂系统的过程。也就是说,不论是我们所熟悉的细胞还是未来我们可能发现的外星生命,生命的本质在于其创造并保持的复杂结构是纯粹随机过程无法轻易产生的。该观点依赖于装配理论(Assembly Theory),这是一种通过“装配指数”和“复制数量”两个指标来衡量物体复杂程度及其分布的理论。装配指数表示构造某物体所需的最短步骤数目,类似于用积木搭建复杂形状所需的步骤。而复制数量则衡量宇宙中该物体存在的副本数。若某一物体具备高装配指数和高复制数量,意味着它由一个非随机、类似于达尔文选择的过程产生——这是生命的真实特质所在。
将生命视作一种物理过程,可以帮助跨越地球生命形态的限制,从而为我们识别各种非传统生命形式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不仅延伸了我们对生命现象的理解,也有助于指导我们在深空探测和人工生命研究中的目标聚焦。像AI系统这样的技术产物,也在这一观点框架下有可能被重新定义为具有某种“生命”特质的实体,原因在于它们能够生成复杂的、有序的结构,并在多个复制体中持续存在和演变。此外,这种视角还将生命看成是一个光谱,而非二元对立的存在。所谓的“活性”是基于对象对其环境所产生的复杂程度和有序系统的影响力。换句话说,越能创造远超过自身输入复杂度的输出,生命的“活性”就越高。
这种定义与我们对人类代理性(agency)的理解不谋而合:高代理性的个体能够塑造周围环境,而低代理性个体则更多被环境所塑造。尽管装配理论为生命的物理定义提供了坚实基础,仍存在诸多尚未完全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如何界定不同层级的“对象”和“构建模块”?在化学层面,分子与原子关系明确,计算装配指数较为便利,但面对如器官、生态系统甚至恒星等复杂系统,则需发展更复杂的数学和物理模型。未来科学的发展或许会推动这些问题逐步被破解,为我们提供更加细致和普遍的生命标准。人类一直执着于寻找与地球生命相似的生命形式,这种方式势必限制了科学发现的范畴。将生命定义为一种普遍的物理现象,超越生物学上的限制,等同于从根本上扩大了我们的视野,就像哥白尼革命改变了人类对宇宙中心的认知一样。
这种转变不仅是科学范式的飞跃,也带来了对于宇宙和生命的哲学上的深刻反思。如今,生命不仅仅是生物学家研究的对象,更成为跨学科领域关注的焦点。物理学、信息科学、人工智能乃至哲学都在试图从不同角度解码生命的本质。基于装配理论,未来的科学工具将能够量化复杂性的演进及复制,并将其作为判断“生命”与非“生命”的依据。这种全新方法不仅推动了外星生命探寻的科学进程,也为我们理解人工智能、自组织系统及生命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路。从宏观宇宙到微观分子,从生物生命体到人工智能,生命作为一种物理过程的观点提醒我们,无论其外在表现如何丰富多变,生命的真谛是其内在的自我组织、自我复制及复杂性维持机制。
只有了解这些根本规律,我们才能在茫茫宇宙中不再局限于狭隘的生命定义,而更广泛、深刻地探索生命的多样性和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