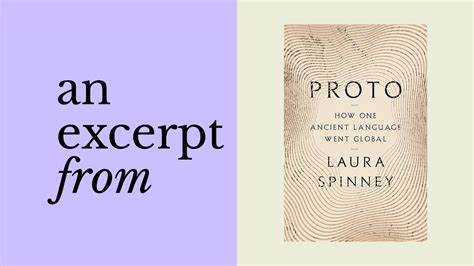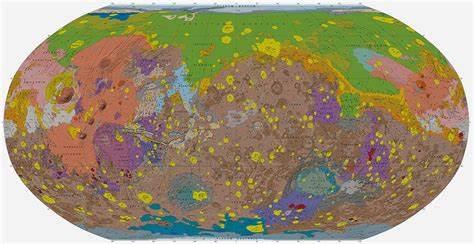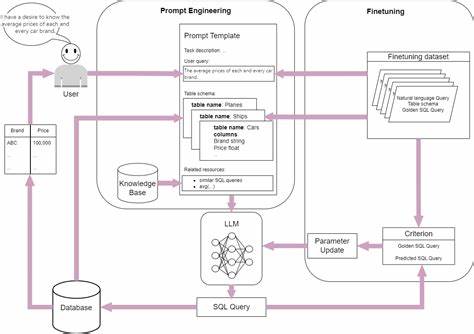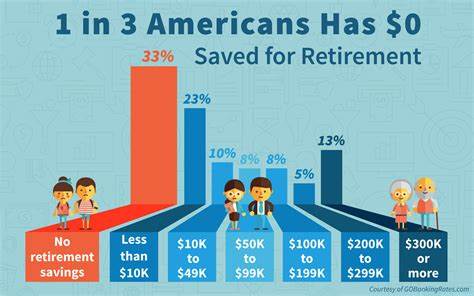英语,作为当今世界最广泛使用的语言,已经成为全球交流的桥梁。然而,围绕英语的地位和未来,学界与公众间的讨论日益热烈:英语究竟是一种“杀手语言”,压迫着其他语言走向消亡,还是它自身正处于衰退甚至“死亡”的边缘?这些问题不仅关乎语言学,也与全球化、文化认同以及社会变迁息息相关。自198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英语一路领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语言。其地位的确立使得它成为跨国交流、科技、商业和文化传播的首选语言,推动了经济和信息的无障碍流动。与此同时,有观点将英语称作“杀手语言”,认为它的扩张压制了许多小语种的生命力,导致语言多样性的下降。对此,芝加哥大学刚果裔语言学家萨利科科·穆夫韦内(Salikoko Mufwene)持不同看法。
他指出,英语的全球扩展大多表现为一种通用语(lingua franca),它可能取代了某些地区的通用语如非洲的斯瓦希里语、亚洲的马来语,但对于当地土著语言的日常使用影响有限。他认为“杀手语言”的标签更多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因为欧洲社会历来强调单语言主义,而非洲、亚洲及其他地区则普遍保持双语或多语并用的稳定状态。事实上,全球多语言共存的现象广泛存在,多语言能力仍是许多社会的常态,而非单一语言的垄断。与此同时,英语自身也在分化成各种方言和变体,从印度洋岛国的英语到美洲、非洲乃至亚洲的多种英语口音,差异日益显著。澳大利亚语言学家尼古拉斯·埃文斯(Nicholas Evans)指出,英语不像拉丁语曾因断绝沟通联系导致的剧烈分裂,而是由于现代媒介如电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普及,英语的不同变体仍共享一个标准的书写系统,使语言保持统一。这种“分层双语状态”(diglossia)可能是未来英语的另一种形态,即书面标准英语与各地方口语变体并存、相互绑定。
语言多样性的问题与语言流失密切相关。目前世界上约有七千种语言,但近一半被视为濒危语言。部分预测指出,未来几十年可能有数千种语言消失,尽管如此,试图复兴濒危语言的努力也在持续,虽然成功案例有限。以色列的希伯来语复兴成为典范,但在威尔士和爱尔兰等地,尽管语言教学投入巨大,少数人真正使用本土语言,且这些语言受到英语显著影响。许多语言学者也顺应现代观点,认为语言的生命力不应仅以使用人数衡量,更重要的是其在文化传承中的活跃度及年轻一代的继承情况。语言进化是必然的,复兴语言往往会呈现出与原生形式不同的新形态。
以色列语言学家吉莉亚德·祖克曼(Ghil’ad Zuckermann)甚至提出,现代希伯来语并非简单复兴,而是诞生了一种希伯来与欧洲语言混合的新语言——所谓“以色列语”。语言保护工作不再仅仅是增加教学资源,而是要深入探寻语言衰败的根源,通常与社会不平等和经济动力有关。语言是一种工具,只能在为其使用者开辟新机遇、提升生活质量时持续存在。虽然当前语言灭绝的数量超过新语言产生,但人们对于语言消失的焦虑有时被夸大,部分原因在于语言变迁和新语言诞生往往在未被充分记录和研究的情况下悄然发生。可以说,全世界仍有诸多“语言热泉”不断滋生新的语言变体和方言,我们或许正在迎来一场语言的复兴浪潮。英语既是强势的全球语言,也正处于动态的进化过程中。
虽然它对语言生态造成一定压力,但在多语并存的时代,其“杀手语言”的论调需要重新审视。未来,英语有可能以多元统一的形态继续发挥全球交流的重要作用,同时为保护和支持其他语言的多样性提供空间。语言的未来不可预知,却充满可能。作为载体的文化、社会需求及技术发展,将共同塑造英语与世界语言图谱的明天。保护语言多样性不仅是学术研究的责任,更是维系人类文化丰富性和认同感的关键。我们应当以开放、包容的视角拥抱英语的全球影响力,同时支持多语言共存和语言传承的努力,让语言之花在全球不同土壤中绽放出更加艳丽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