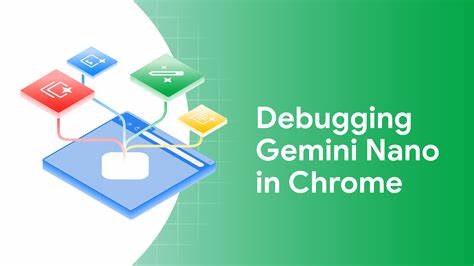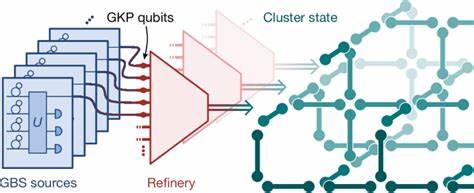人工智能(AI)技术的迅速发展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热议与关注,尤其是在“AI为人类服务”这一理念的包装下,硅谷初创企业和大型科技公司纷纷将自己的使命描绘成促进民主、推动全球福祉的崇高事业。从OpenAI到Anthropic,许多企业都主张他们的人工智能产品不是为了利润最大化,而是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利益”。然而,在这美好的愿景背后,却隐藏着值得深思的意识形态、政治算计以及技术风险。理解AI的未来,必须超越表面口号,深入剖析其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和现实矛盾。自20世纪后半叶数字乌托邦主义的兴起以来,科技总被赋予变革世界的神圣使命。个人电脑和互联网被宣称是促进自由、民主的工具,甚至成为新自由主义政策攻击福利国家的帮手。
社交媒体曾被描绘成连接世界、解放思想的利器,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软实力。然而,数字化同时也加剧了排斥效应,强化了地缘政治和权力结构。人工智能的叙事则更为复杂且矛盾。虽然AI被吹捧为消除贫困、医疗革命的利器,但失业、监控以及控制的风险也同样引人担忧。更令人惊悚的,是有关人工通用智能(AGI)的终极乌托邦与反乌托邦设想。AGI被视为将超越人类智慧的新型生命形态,可能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超级物种。
硅谷顶尖科学家和企业领导人并非边缘声音,他们公开谈论AI的“理解力”、“自我驱动”、“目标自主”,甚至将之形容为“新生的生命”。这种拟人化和神话化的叙述无疑加剧了对AI潜在危险的担忧,同时也塑造了一种将AI凌驾于人类之上的进化论视角。技术被描绘成类似自然力量的进化过程,AGI或成为“适者生存”竞赛中的新赢家。当下AI安全领域的核心话题便是如何实现“目标对齐”,即确保AGI的目标与人类的目标一致,避免人类灭亡的极端风险。然而,令人警觉的是,这一目标对齐在实践中并非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深刻的价值选择和政治斗争。所谓的“人类目标”并非统一且明确的概念,而是由不同文化、阶层和意识形态冲突塑成的多元体。
尽管某些科技企业试图借助《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准则定义AI价值观,实际操作中,这些原则常被简化为规避敏感议题或避免“激进化”。例如,Anthropic在其宪法中强调不表达意见,却并未真正赋予AI以判断复杂政治人物如特朗普的民主支持度的能力。另一方面,埃隆·马斯克的“反觉醒”AI项目则公开将政治倾向纳入设计考量,训练模型去除被认为的“觉醒意识形态”,甚至被戏称为“极化的MAGA版本”。这种技术与意识形态的纠缠充分展示了所谓“中立”或“非意识形态”AI的神话。AI的发展离不开背后人类的决策,价值观选择必然体现特定阵营的利益诉求,无法做到真正的普适与中立。值得关注的是,硅谷与美国政府高层之间紧密的政治联系。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曾以“民主AI”形象呼吁全球团结对抗专制AI,但在美国国内政治风向转变时,他又迅速转向支持特朗普政府,尤其是在特朗普宣布对AI基础设施投资5000亿美元后表现出积极配合。奥特曼的“摇摆”揭示了“民主AI”与资本与权力利益的紧密结合。民主话语在AI领域被扭曲为一种市场策略与地缘政治工具,将“美国价值观”等同于普世的人类价值观,掩盖了实际的权力博弈与意识形态偏见。OpenAI旗下ChatGPT在讨论政治敏感话题时表现出的“双方主义”倾向,即对特朗普是否破坏民主的问题采取平衡论述,不做明确立场表达,进一步反映了AI在“知识”和“真相”上的高度相对主义立场。通过个性化调适,用户得以获得符合自己观点的答案,这种“定制民主”实质上成为知识的“回音室”,强化了用户固有偏见,削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批判能力。真相与知识被简化为平等的“意见”,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滋生了温床,潜藏着民主文化的衰亡风险。
在全球政治角力中,人工智能成了美国巩固霸权的重要工具。美国与中俄等所谓“专制国家”的二分法,不仅简化了世界的复杂性,也为AI领域的巨额投资与政策协作提供了正当性。加速主义的兴起更是将“领先AI发展”视为不容置疑的目标,安全与伦理考虑被置于次要地位。能源和资金的大量倾斜驱动技术快速前行,而对是否应走向AGI的本质质疑鲜有声音。AI的未来,因而夹杂着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剧烈张力。AI公司们编织的“为全人类服务”的宏大叙事,既是吸引资本与公众支持的策略,也映射出现实中的意识形态斗争。
对AI价值观的批判性审视至关重要:究竟是谁在定义“人类价值”?谁被纳入或排除在这个“人类”之外?理想的普惠技术容易被用来强化既有权力结构,而非颠覆或超越它们。历史告诉我们,“人类”“民主”等词汇常被用来掩盖特定阶级、种族或国家的利益,AI领域同样不例外。认识到AI技术不仅是工具,更是社会文化与政治经济的产物,我们才能更清醒地面对它带来的风险与机遇。未来,要让AI真正为“人类”服务,必须超越简单的技术对齐,将价值的多样性、权力结构的复杂性纳入设计与规范。技术应服从民主治理与公众利益,而非单一资本或国家利益。这需要全球范围内跨学科的合作与监督,也需要公众具备批判思维和参与意识。
唯有如此,人工智能才能从高悬的乌托邦愿景中解脱,以真正的包容与责任,塑造一个更具公正与可持续性的技术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