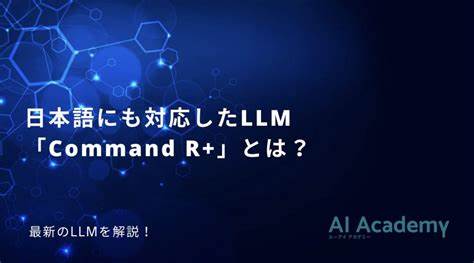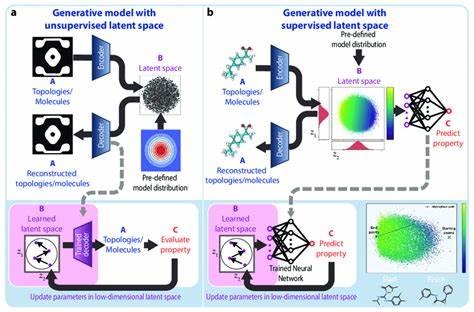近年来,极右政治势力在全球多个国家迅速崛起,其表现形式虽然因地制宜,却呈现出惊人的相似性。人们习惯性地将这种现象归结于某一特定政治人物的煽动或某一党派的政策,却忽视了其背后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结构。这场所谓的“极右蔓延”,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反应,是对20世纪后半叶工业繁荣时代结束以及数字化转型带来的剧烈社会变革的深刻反响。极右势力的支持者大多来自那些曾经在传统产业中拥有稳定劳动岗位的白人工人阶级社区,他们的身份认同和价值感因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而遭受重创。曾几何时,煤矿工人、钢铁工人、造船工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里不只是劳动场所,也是社区和家庭生活的核心。这些岗位虽然危险且辛苦,但足以保障生活的体面和尊严。
这些劳动群体通过团结和集体协作获得地域和国家层面的认可,也因此形成强烈的自豪感和归属感。随着工业的衰退,尤其是在西方发达国家,这些社区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萧条和社会断裂。煤矿和钢铁厂的关闭不仅带走了就业,也带走了自我认同和社会尊严。这些曾经的“中坚力量”突然发现,传统的技能不再被需要,取而代之的是需要高学历和复杂技术知识的新兴产业。面对数字革命的浪潮,缺乏教育投资和资源的他们感受到被抛弃和边缘化。政治上,极右力量往往抓住了这些人的不满和焦虑,通过对所谓“文化威胁”的强调,如反移民、反全球化和反精英主义,激发他们的愤怒和恐慌。
尽管这些支持者中许多人对极右政党的具体政策知之甚少,但情感上的共鸣和对现状的不满驱使他们支持那些承诺“恢复过去辉煌”的领导人和政党。这些政治势力所勾勒出的往昔黄金时代,无疑是20世纪中叶工业黄金期的侧影,那是一个劳动者被尊重,社区生活绚丽多彩的年代。极右势力的兴起是对这种历史记忆的一种扭曲化表达,试图通过排斥“他者”和颠覆现有的社会制度,重塑那种他们认为被剥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值得注意的是,这不仅仅是某一国家的特殊现象。美国的MAGA运动,英国的改革党,德国的选择党( AfD )和法国国民联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都有着惊人的群众构成相似性:他们大多是教育水平较低、生活在经济衰退地区的白人。这种现象的跨国性揭示了极右势力本质上是一种全球性的社会病症,是应对快速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带来突变压力的错误反应。
在美国,公众视线几乎全部聚焦于特朗普现象,认为极右崛起是其个人魅力和政策激进的直接结果。但从全球角度看,特朗普仅仅是这种大病症的一个具象表现,是症状而非根源。确实,特朗普的煽动和媒体影响加速了这种势力的传播,成为全球极右运动的“超级传播者”,将类似思想输出到巴西、匈牙利、英国等多国。但回归到根源,我们仍需看到的是社会结构的巨大断层,是那些被遗忘的工业城镇人民无法在新经济图景中找到自己的定位感。这种社会断层如果得不到正视和修复,极右势力的感染不仅不会减少,反而会如洪水猛兽般肆虐。极右的支持者并非盲目敌意的激进分子,更多是迷失在新时代变革中的普通人。
他们渴望被看见,渴望尊重,更渴望拥有掌控自己命运的能力。简单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争辩无法触及他们的核心痛点,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技能提升帮助他们重新建立与现代社会的连接。教育不应只是象征性口号,而应成为战略性国家优先事项。面对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革命等21世纪的新经济模式,只有具备相应知识和能力的劳动者才能真正参与进来,获得尊严与安全感。社会政策要注重从社区根基做起,为这些边缘群体构筑安全的过度期和公平的晋升通道,也需尊重他们的历史文化与集体记忆,让他们觉得自己依然是国家故事不可或缺的部分。这并不意味着要复刻过去的工业时代,而是要创造一种包容且动态适应的社会结构,为不同背景和技能的人提供平等的机会。
文化上的对立,如排外和仇视精英,以极右民族主义者为例,往往只是掩盖深层经济焦虑的表象。唯有脱下意识形态的外衣,以人性化、社会包容的姿态面对困难与挑战,才能真正减少极右势力的滋生土壤。极右蔓延是对现代化世界深刻矛盾的反映,是传统身份认同与数字未来之间的撕裂。它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治人物的问题,而是全球化时代的共通课题。只有通过全面、包容且切实的社会经济改革,尤其是在教育和就业方面取得突破,才能迎接这个挑战,推动社会朝向更加公平与稳定的未来。这场斗争不但关乎政治版图的重塑,更关乎数百万被变革浪潮席卷的平凡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