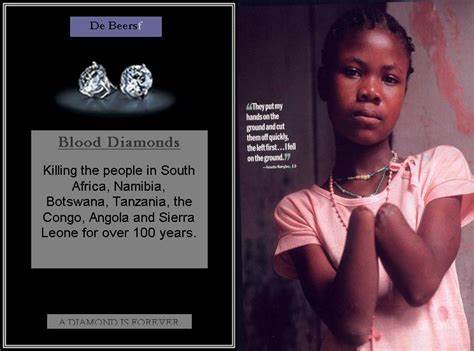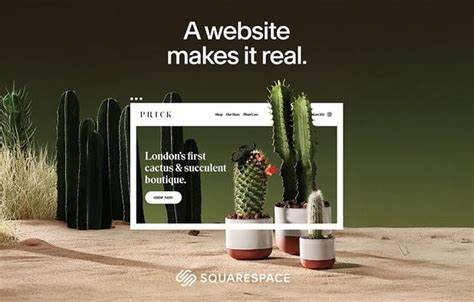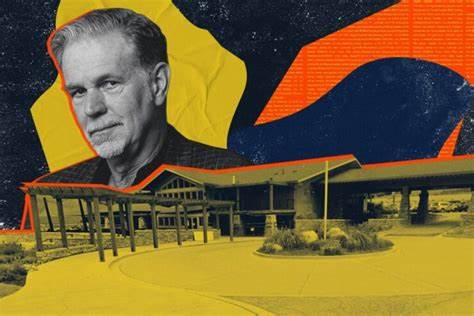1957年苏联发射“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不仅标志着人类进入太空时代,更激发了美国强烈的国家竞争意识,带来了深远的科技与教育变革。这一事件被称为“斯普特尼克时刻”,美国随即加大了对教育领域的投资,尤其是在数学、科学和外语方面,通过设立先进的科研机构如高等研究计划署(ARPA)、放宽移民法规吸引海外人才以及减少关税壁垒等手段,展开全面反击与竞争。然而,面对近几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崛起,尤其是标志性的“DeepSeek”项目,美国的反应显示出截然不同的态度,更多表现为焦虑、保护主义和退缩。这种现象引发了关于为何相似的国际技术竞争背景下,美国反应迥异的深层次讨论。 “DeepSeek时刻”实际上不仅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更是象征着更广泛的中国崛起进程——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制造国、电力生产大国,以及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军队的国家。尽管有人质疑DeepSeek的技术意义,认为其并不具备足够的震撼力或威胁性,但这种看法忽略了DeepSeek背后所代表的结构性挑战。
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复杂交织,尤其是在经济、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存在着许多不确定性和分歧。 有观点认为,斯普特尼克激发强烈反应,缘于当时被视为存在生存威胁;而DeepSeek及中国崛起并未被多数美国人视为“存在性威胁”。确实,从理性角度出发,中国经济实力强大,虽无苏联式的革命意识形态,但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值得注意的是,威胁的感知是否足够强烈并不足以解释美国政策上的松紧,因为强威胁往往促使采取更为防御和限制性的政策,例如更高关税、收紧移民等。 另一种解释涉及人口结构变化,认为当前美国中位年龄上升,选民群体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更年长、更富裕且种族构成更为多样化,因而更为保守和内向,趋向风险回避。然而这一解释存在矛盾:特朗普支持者并非典型的风险回避群体,他们经常推动激进甚至冒险的政策变革,显示出复杂的政治心理规律。
再者,美国作为“战争-福利”国家,财政与政治空间有限,这种现实约束削弱了政府发起大规模科技竞争项目的能力,但更深层原因在于人口和精英的文化心理变化,即我们已经“失去想要大规模冒险和探索的意愿”。 经过多方面权衡,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是“零和思维”的兴起。零和思维本质上强调资源与利益的有限性,认为一方的获得必然建立在另一方的损失之上,从而导致竞争对抗的加剧,难以形成共赢局面。在这种心态下,开放贸易、鼓励移民、增加高校及科研投入被视为“利益再分配”,会被某些群体解读为“他们”剥夺了“我们”的资源和机会。 零和心态滋生贸易保护主义,因为当其他国家获益时,零和思维者认为自己失去了利益;反对移民则基于“移民获利,原居民受损”的简单对立假设;连大学和科研机构也被视为精英阶层迎合自身利益的工具而非公共资源。这种“我们”和“他们”的尖锐划分削弱了国家层面的团结和协作,阻碍了创新的公共投资。
有趣的是,零和思维不仅解释了美国对中国技术挑战的防御性反应,还因这种外部威胁而加剧。研究表明,在感受到威胁时,个体更容易产生零和心理,表现出竞争性强和对社会不信任等特征。此类心态还与负面情绪、贪婪以及对社会制度的不满紧密相关,助长了愤怒与民粹主义的兴起,削弱了人们对合作与共享利益的信心。 此外,零和思维在不同群体间有明显分布差异:年轻人往往更少零和思维,因为经历经济增长时期的人更倾向于相信“蛋糕可以做大”,而经历经济停滞的人则更容易陷入“你赢我输”的窘境。移民一般表现为低零和心理,因其更易感知成长机会。 零和陷阱带来了潜在风险,执迷于零和思维将促使制定零和政策,诸如限制贸易、阻碍移民、削减科研投入,而这些政策往往无法带来真正的增长,反而可能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和创新能力衰退,从而使零和世界观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回顾历史,斯普特尼克事件之后,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一种以扩张为导向、对未来充满乐观的竞争心态,强调通过投资科技教育与开放交流来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反观当前,随着全球化进程放缓、国内不平等加剧、政治极化升温,公共信任缺失,零和心态蔓延,导致社会对变革的抵触和守旧心态加强。 除此之外,技术环境的根本性变化也影响了应对策略。过去,技术突破主要由政府主导推动,需要集中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如阿波罗登月计划、曼哈顿计划等。而当今技术创新正由大型科技企业驱动,资本充裕、创新路径多元,政府的角色转变为监管和协调者。尽管如此,国家层面的政策引导和战略投入依然不可或缺。
面对中国的快速追赶,美国应如何突破零和思维束缚?强调非零和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加强对教育、基础科学以及技术研发的投资,推动开放与合作,调动多元文化力量,创造包容性创新环境成为关键。重新点燃国家使命感和共同愿景,有助于凝聚社会共识,防止陷入零和竞争的恶性循环。 同时,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挑战与担忧。AI等颠覆性技术不仅改变经济结构,还引发职业替代、隐私安全、伦理规范等诸多议题,部分公众对未来充满焦虑和怀疑,对技术持保留态度。这种心态反映了人们在高速变化时代的心理压力,也影响着社会政策的支持度。 总的来看,“斯普特尼克时刻”与“DeepSeek时刻”的对比不仅体现了技术竞争的表象,更深刻折射出美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转型。
零和思维的兴起掣肘了美国传统上的开放创新优势,阻碍了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削弱了应对全球挑战的能力。要实现真正的技术领先和国家复兴,必须超越零和对立,找回积极向上、共赢共享的发展思路。 未来,全球科技竞争将更加复杂且充满不确定性。美国如何在保持自身创新优势的同时,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合理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将成为决定其长远发展的重要课题。学界和政策制定者需深入理解零和思维的根源和影响,设计科学合理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文化的积极转型,实现科技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与可持续发展。这样,才能在新时代开启新的“突破时刻”,为人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