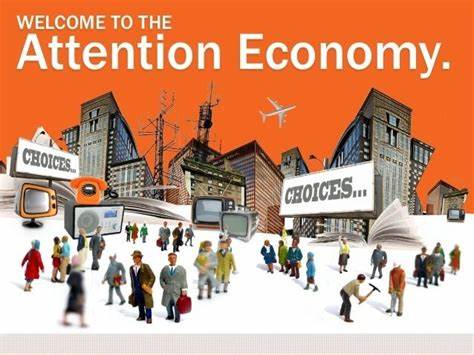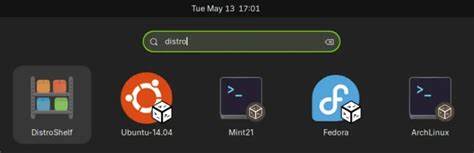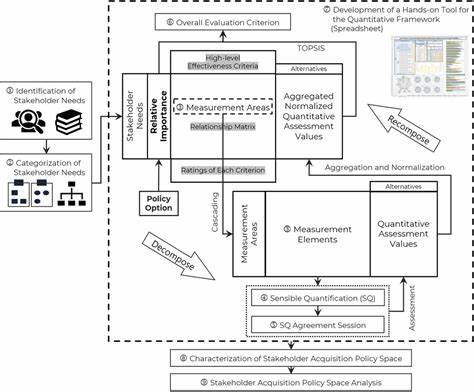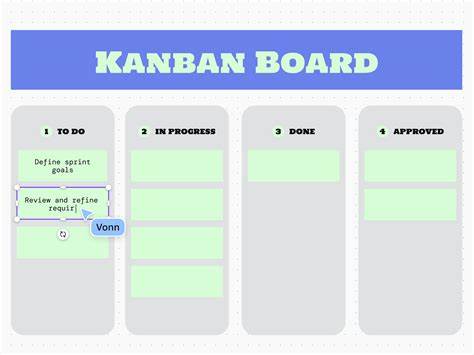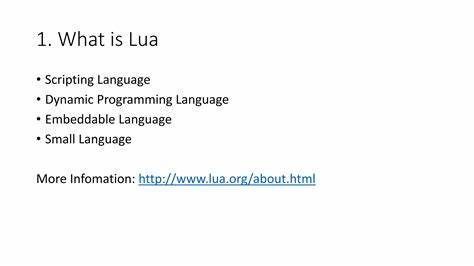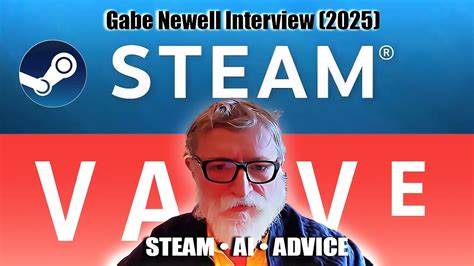19世纪的美国,廉价日报的迅速崛起不仅成为信息传播的一场革命,更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和思考模式。报纸从原本被视为高雅文艺追求的陪衬,转变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这标志着现代注意力经济的诞生。注意力不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一种被争夺和交易的稀缺资源,这一现实在19世纪的报业中得到了最早的体现。早在南北战争期间,文学家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将面包和报纸视为生活的两大必需品,当时的人们每日生活几乎是从一份份报纸的最新报道中寻找刺激与慰藉。报纸凭借电报带来的快速信息传递,以一种“神圣的权利”主宰着公众的视听感受,主导着那个时代的社交和思维方式。最初,很多人认为这种信息依赖只是战争时期的特殊现象,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在美国社会的渗透愈发深厚。
到19世纪末,这种廉价日报的普及导致信息传播速度与广度大幅提升,报业不断扩大版面和发行频率,成为日常生活的主旋律。美国各大城市街头,小报贩高声吆喝新闻内容,这不仅是对商品的推销,更是对人们注意力的直接争夺。新闻报道以火灾、谋杀、骗局、以及各种轰动一时的事件为卖点,制造轰动效应,刺激公众购买欲望,也催生了“注意力经济”早期的商业模式。人们对新奇事物的渴望,促使他们在繁杂的信息中漂移,持续寻找最新、最引人关注的话题。与此同时,这种过度的信息轰炸也引发了一批知识分子的担忧和批评。著名思想家亨利·戴维·梭罗便提醒大众要谨慎选择信息消费内容,应保护自己的注意力不被琐碎和低质信息所掩盖。
他认为,过度沉溺于当下琐碎的新闻将侵蚀人的精神世界,让读者丧失深度思考的能力。从他的角度看,人们应更多关注永恒的智慧,而不是每日不断更新的新闻轰炸。19世纪下半叶,报业的爆炸式发展让信息量成倍增长,城市居民在快节奏的生活中仍能花大量时间阅读报纸,这一点曾被海外观察者惊叹为“全世界最繁忙的人们却有那么多时间阅读”。然而,文化评论者担心这种现象将导致公共智力下降。报纸内容越发通俗、直接,语言趋于粗俗,综合素养受到削弱。这种现象在当时被称为“报纸化”的心智状态,即大众读者的注意力被碎片化、浅显化的信息所占据,深度阅读和严肃文学则渐渐被边缘化。
著名心理学家兼记者威廉·詹姆斯·斯蒂尔曼曾指出,廉价日报对美国民众的心理发展具有负面影响,并担忧这种信息消费方式会助长政治极化和谣言扩散。事实证明,媒体在竞争读者关注的过程中,往往会迎合读者已有的偏见,强化信息泡沫,削弱理性判断。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对新媒介的担忧几乎是每一代人的宿命。从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对文字的批判,到18世纪对小说泛滥的焦虑,再到20世纪文学家海明威借鉴“新闻直白”风格创新写作,每一次新技术或表现形式的出现,都引发类似的恐慌与质疑。然而,时代变迁也表明,创新虽然带来挑战,也伴随机遇。唯一在不断变化的,是人们如何适应这些新媒介对注意力和认知的影响。
进入数字时代,算法与人工智能对人类注意力的影响远超以往。机器不仅能够准确预测并筛选个体喜好的内容,甚至可以代替人类完成创作与沟通。这种前所未有的便利极大地降低了对深度思考的需求,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即时和符合用户预期的信息体验。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新的精神焦虑,人们担心在数码洪流中,思想能力可能被进一步弱化,心灵将被碎片化和肤浅化的内容淹没。就像梭罗在19世纪预见的那样,智识之路若被机械化铺开,反而可能阻碍精神世界的自由流淌。现代社会的“一切都可以算法预测和生成”的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反思,面对海量信息,如何守护自身的注意力,保持精神的纯净和敏锐。
回望19世纪报业的兴起,我们看到的是现代注意力经济的雏形。在信息成为商品的时代,每一次传媒变革都在重新塑造人类的心智结构和社会行为模式。理解这一历史进程,既是对过往的回顾,也是为未来数字时代的注意力使用提供启示。伴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唯有学会有意识地管理和选择,才能在信息浪潮中稳健前行,让“注意力”这一珍贵资产重新焕发其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