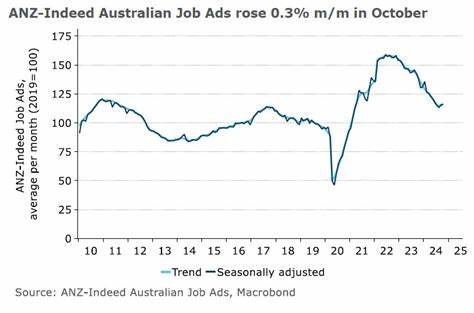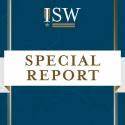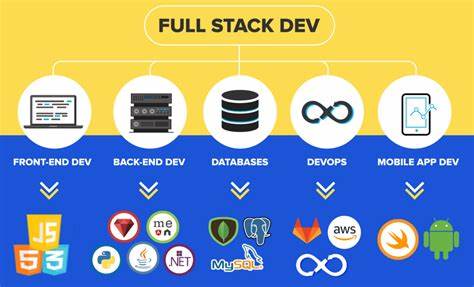《America, América: A New History of the New World》是历史学者格雷格·格兰丁(Greg Grandin)的一部重要著作,致力于重新审视美洲大陆五个世纪以来的历史进程,特别聚焦于美国与拉丁美洲之间错综复杂的政治、文化与国际关系。本书不仅为拉丁美洲在塑造国际秩序中的角色赋予了应有的地位,也深刻揭示了美国扩张主义与拉美多民族共和体制之间的对比与冲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启示意义。格兰丁的研究始于西班牙征服时期,这一选择在编辑建议下成为本书的起点,也使得本书的结构呈现为嵌套的“双重书写”——一方面是拉美理念孕育国际法与秩序的“内核”,另一方面则是贯穿几个世纪的整体历史框架。拉丁美洲受西班牙殖民影响,逐渐构建起以尊重边界与拒绝征服权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理念。拉美诸共和国在独立战争后形成了一个多民族的政治共同体,彼此间的国界虽模糊,但大致稳定,土著族群被视为国家组成部分而非外族。此外,拉美国家面对欧洲殖民势力“再殖民”的威胁以及美国扩张主义的现实挑战,共同推动了所谓“美洲国际法”的形成。
这一体系旨在限制大国野心,维护所有国家作为主权平等体的完整性。美国独立后,以扩张为天命,推行从东向西的领土拓展,内嵌着地缘政治、棉花资本主义、边疆机遇和白人至上主义因素。相较之下,拉丁美洲国家奉行不同的发展路径,这种差异也奠定了两者在国际关系理念上的根本分歧。当1823年美国发布门罗主义时,拉丁美洲抱持乐观态度,视其为反殖民主义的认同。然而,随后的历史证明,美国并未遵循这一原则,多次干涉和强占拉美领土与政权,从墨西哥、波多黎各、巴拿马到委内瑞拉、海地和尼加拉瓜,频繁使用武力与经济手段介入。这促使拉美法律界积极推动对美国行为的国际法律抗争,形成了如卡尔沃原则(Calvo Doctrine)与德拉戈原则(Drago Doctrine)等重要国际法条文,这些条文反对非本国居民享有特别的治外权,以及针对债务催收采取军事手段的做法。
这些理念最终在国际外交舞台逐渐获得认可,成为现代国际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最具权威的部分聚焦于美国内部的分歧:一方面是主张单边军事强权的鹰派,另一方面崛起的新一代国际主义者,他们试图借鉴拉美提出的原则构建新全球秩序。拉美国家利用这种局势,赢得了一些长期诉求的外交让步。格兰丁详细描写了从1889年至1919年间,第一届泛美会议、1907年海牙和平会议和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博弈,尽管拉美原则未能完全进入伍德罗·威尔逊的国际联盟架构,但其影响深远。1933年蒙得维的亚泛美会议成为转折点,时任美国国务卿考德尔·赫尔在富兰克林·罗斯福领导下接受了“不干涉主义”原则,加之签署了贸易协定,开启了“善邻政策”的新时代。此政策为二战中西半球的团结奠定了基础,拉美国家得以在实现国内进步的同时,也影响了美国企业如标准石油在区域的经营空间。
这种合作关系体现了拉美国家在国际政治中的主动参与,而非单纯受制于美国霸权。然而,战后冷战格局迅速瓦解了这种基于反法西斯团结的合作,美国重新诉诸老路,将帝国主义外衣换作反共国际主义。雷根撤出国际法院、布什入侵巴拿马,象征性的封闭了美国对威尔逊国际主义原则的支持。格兰丁以此提醒读者:“善邻政策”的辉煌短暂,但其理念仍是现代国际法与区域合作不可或缺的根基。格兰丁的“外部书”部分则回溯到更早的历史,从清教徒与征服者的起源,哲学思想家约翰·洛克到西班牙的弗雷·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Fray Bartolomé de Las Casas),展现了两种迥异的文明轨迹。西班牙殖民制度基于“人类皆一”的天主教普世主义,尽管对土著的奴役与屠杀充满矛盾与质疑,但在法律主义、包容性和社会正义方面孕育了潜在传承,这些价值贯穿拉美独立战争及以后的社会变革,如解放神学与墨西哥1917年宪法中的社会权利。
相较之下,北美清教徒的理念则基于“上帝选民”的反普世主义,视土著土地为可夺取的自由之地,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种族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从“眼泪之路”的土著流离失所,到智利阿连德政府被推翻,再到伊朗门丑闻等事件,这种基调在美国历史中反复显现。格兰丁通过对比两种历史脉络,阐释了美国在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上的兴衰历程,从而为当今国际关系提供深刻借鉴。《America, América》不仅是一部历史学著作,更是一面镜子,映照出北美与拉丁美洲之间错综复杂的命运交织与未来走向。它提醒我们,拉美国家不只是历史上的受害者或被动观察者,而是推动现代国际法与全球秩序形成的关键力量。对研究美洲历史、国际关系、殖民与后殖民问题的学者和公众而言,这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重要著作。
格兰丁凭借详实的档案资料、生动的外交往来记录以及深刻的历史洞察,使这部书成为解读新世界历史不可忽视的经典之作。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和国际秩序多极化的当下,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尤显重要,为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体系提供视角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