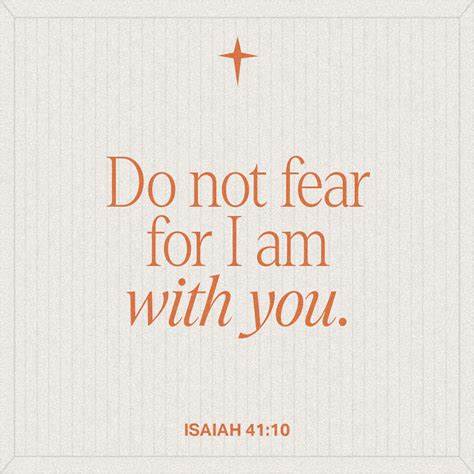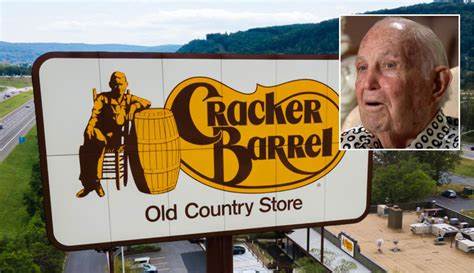在当今全球政治舞台上,极右势力以一种特殊的形式迅速崛起,成为许多国家社会分裂与不安的主要推动者。诸多观察家和学者对这种现象深感忧虑,尤其是当他们发现现实中的社会民主派和自由派 - - 那些自诩为民主守护者和社会正义推动者的力量 - - 实际上在其职责上表现出令人失望的被动和妥协。面对极右的迅猛发展,重要的反思问题是:我们真的害怕极右势力会做我们自己未曾做过的事吗?换句话说,极右的恶行是否其实已是当前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和自由民主派早已实施和纵容的行为的延续?或者极右仅仅放大了已有的社会问题和制度性缺陷,以极端形式表现出来? 首先,极右势力的流行与当前全球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失败密切相关。在经济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浪潮下,许多传统社会保障体系被削减,公共服务日益紧缩,工人阶级和农村社区的组织纷纷瓦解,而自由派政治家们往往默许或推动这些政策的实施。这些政策的后果是社会分层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信任和社会资本受到侵蚀,普通民众感受到被边缘化和忽视。极右势力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找到了滋生和壮大的土壤。
他们通过利用社会个体的孤立无援感,塑造敌对他者和替罪羊,制造族群对立和社会撕裂,借此动员一部分失望和愤怒的选民。与此同时,极右领导人通常无视科学共识,否认气候变化,反对全球合作,支持军备扩张和新一轮冷战氛围,这些主张与传统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形成鲜明对比,但又在部分基层民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双重且复杂的角色。从表面上看他们撑持自由、多元和包容的原则,参与民主制度的运作,推动部分社会进步,但实际上,他们往往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市场逻辑,推崇财政紧缩政策,减少社会福利,限制劳工权益,纵容私有化和金融投机。这些行为极大地削弱了人民对民主制度的信任感,使得民众开始怀疑自由派所宣称的公正和平等承诺。 甚至在国际重大冲突中,自由派国家往往表现出选择性沉默或被动支持暴力和侵略。
如巴勒斯坦遭遇的持续暴力中,一些自由派政府未能采取积极有效的立场,反而通过各种间接方式助长了压迫的态势。这种现象不仅暴露了他们在维护人权和国际正义上的缺位,也为极右势力的宣传制造了论据,即传统政治精英被腐败和无能控制,只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文化层面上,现代自由主义哲学陷入了学术性和抽象性,更多成为电视辩论和媒体广告的道具,缺乏深刻的道德指南和实践意义。自由派文化缺乏生机和创新,没有打造属于自身的深厚文化底蕴,面对极右的极端民族主义和暴力扩张时显得软弱无力。另外,极右并非像传统法西斯主义那样拥有明确哲学体系和知识分子引导,他们借助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碎片化幻想和消费主义梦境,显示出一种急功近利且充满恐惧的政治姿态。 在军事和政策层面,全球北方国家,尤其是欧美国家,是极右势力的中心点,这些国家掌控着世界上绝大部分军费开支和海外军事基地。
军事预算的膨胀往往以社会福利的缩水为代价,这种资源倾斜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同时也使得国际关系更加紧张和充满不确定性。反观极右领导人,他们以"强权治国"和"秩序至上"为旗号,强化警察暴力,推动民族排外和社会打压,破坏公民自由。 所谓"恐惧极右将做我们没有做过的事",其实是对现实的误读和掩饰。自由派和社会民主党在经济、政治和社会领域曾经的妥协和缺失,为极右现象的发生创造了条件。当我们看到极右制造社会分裂、压制弱势群体、推崇暴力政治、否认气候科学,我们不应将其视作前所未有的现象,反而更应反省那些自由民主派自身未曾正视的矛盾和责任。 因此,真正的战斗不仅仅是反对极右派的选举斗争,更是对现有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反思和革新。
全球南方的社会运动和思想创新,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路线。他们主张重拾传统文化活力,回归群众基础,加强基层工人和农民组织的建设,寻求经济正义和社会公平。理念上的脱离西方新自由主义模式,寻求符合本土实际的独特道路,是抗击极右和重建社会信任的关键路径。 此外,重大国际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军事化、以及人权危机,需要全世界社会力量的联合和协调,而非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真正的领导者应当承担起伦理和社会责任,推动包容性政治,促进社会福利,抵御金融资本的过度扩张,恢复公共领域的活力。唯有如此,才能有效抵御那些以恐惧和仇恨为燃料的极右势力,重塑更公平和可持续的未来。
总结来看,极右崛起是一个复杂且多层次的社会政治现象,其背后是既有体制的失败和自由派的妥协。面对极右威胁,社会不能一味恐惧和抵制,而应当审视自身的责任及历史教训,推动全面的政治与文化革新。在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不断加速的时代,建设一个团结、公正且具有人文关怀的社会,是防止极端主义扩散的根本对策。唯有如此,我们才不必惧怕极右会做我们"未曾做过的事",因为我们早已在践行制度性的改变,而极右则是其畸形的反映与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