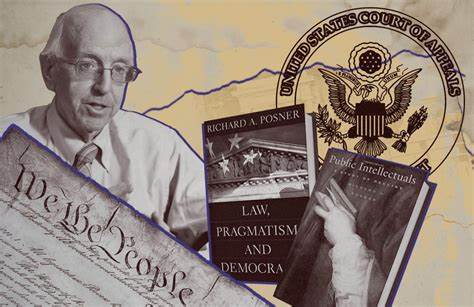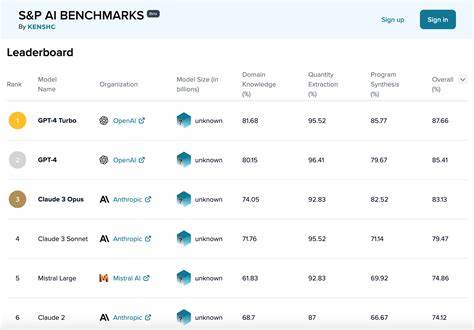理查德·波斯纳,这位法学界的巨人,自20世纪下半叶起便以其卓越的学术成果和司法实践闻名于世。他的名字几乎成了法律与经济学结合的代名词,他撰写的著作多达六十本,涉及从性别问题到小行星撞击的广泛话题,发表的司法意见超过三千份。他不仅是美国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法律学者之一,也是90年代自由市场运动和法经济学理论的核心人物。然则,他的职业生涯和思想轨迹远不止于此,波斯纳的故事充满了矛盾与复杂,也正因如此,他成为一位值得深入解读的传奇人物。 波斯纳的早期经历塑造了他未来的道路。出生于1939年,从小便展现出非凡的智慧,他的母亲甚至在他幼年时教他阅读荷马史诗和莎士比亚。
十六岁进入耶鲁大学,他选择英文专业,撰写了关于叶芝晚期诗歌的三百页学位论文,后来进哈佛法学院深造并担任《哈佛法律评论》主编。尽管起初对法律的热情并不高,但在与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经济学家及芝加哥大学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接触中,他逐渐形成了以经济分析视角审视法律的哲学。 1969年,波斯纳加入芝加哥大学,成为该校法学院的重要人物,专注于将经济学原则应用于法律体系的研究和教学。他的《法律经济学分析》成为同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教科书之一。他的学术使命感和强烈的自由市场信念,使他不仅在理论层面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影响了政策制定与司法实践。1981年,他被任命为美国第七巡回上诉法院法官,尽管最初对此身份持犹豫态度,但随后毅然承担起司法职责,并在任职期间保持了惊人的工作效率和著述创作频率。
在担任法官期间,波斯纳的司法观点鲜明且常常引发争议。他坚信法律应服务于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强调效率重于形式正义。他曾在涉及苹果与摩托罗拉的专利诉讼中公开表达对专利制度潜在弊端的怀疑,拒绝以传统法理学方式认定侵权行为,而是从经济效益角度审视法律规则的合理性。波斯纳认为市场虽无情,但这种无情是其维持活力与效率的根本特征。他对犯罪问题持严厉态度,强调惩罚的必要性,甚至对囚犯享有宗教自由权感到困惑,认为守法是享受诸多权利的前提条件。 他的言谈举止和司法风格常常体现出尼采式的冷峻和现实主义:社会由“狼”和“羊”构成,具有野心和能量的“狼”自然攀升至权力顶峰,而理想主义的社会正义论调在他看来不过是空洞口号。
他以对批判种族理论的尖锐批评而知名,指责其抱怨、诉诸故事叙述和身份政治,缺乏深入社会现实的分析,甚至贬低其在法学院中的地位为“法律教育的耻辱”。这些观点使他在当代法学界尤其是进步派圈内极具争议。 波斯纳的司法哲学拒绝传统的文本主义与原旨主义,他对法律形式主义抱以怀疑甚至讽刺态度。他指出,司法判决不仅难以通过文献和原始意图完全确定,法官本质上必须根据政治意识形态、个人经历和心理因素作出价值判断。他主张法律应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传统和文本原则不过是工具而非禁锢。此观点令他与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针锋相对,前者视历史和文本为可被弃用的工具,后者坚持法条和传统的重要性。
由于波斯纳的个性独特且观点颇为激进,他尽管才华横溢,却未被视为当年最高法院的合理人选之一。他曾公开表达过对法律职业人士的冷漠和自负态度,自比猫的冷酷与狡猾,性格中的“残酷”特质也令其难以与政治力量和司法体制完全契合。此外,他的“婴儿买卖”经济学观点,以及对司法自由裁量权的坚持,也为他争议注入了难以调和的元素。 在其司法生涯逐渐后期,波斯纳的思想与立场发生显著转变。曾极力主张司法克制的他,在后期裁决中支持同性婚姻权利,反对对劳工及少数族裔的歧视立场也更为鲜明和激进。他开始自觉挑战宪法权力分立,公开承认司法机构在某些情况下在政治功能上的介入。
与此同时,他在审判过程中的举止亦显出越来越多的个人化和不循常规,亲自进行现场调查、网络搜寻,以至亲身体验案件情形,皆开创了前无古人的司法风格,有时甚至引起同行的不满。 行至职业尽头,2017年波斯纳退出联邦法院体系,创立了一家为无力聘请律师的诉讼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的诊所,试图帮助“无律师”诉讼者。但由于需求远远超过供给,诊所难以持续运营。两年后,随着诊所运营者提出诉讼,波斯纳被曝罹患阿尔茨海默氏症,生活状态逐渐隐退。 他职业生涯呈现出一幅丰富且矛盾的画卷,一方面在依法治国的领域贡献卓著,将经济理性引入司法实践,拓宽了法律的视野;另一方面,他对宪法和司法传统的藐视以及近年来行为上的放纵,让人们对司法权威和公信力产生了忧虑。多位法学家指出,波斯纳的言论和行为在动摇公众对司法独立与中立性的信心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
纵观波斯纳的一生,他是一个不断挑战常规的思想家,一名既具冷静严谨又难免矫揉造作的法官。他以自由市场经济学为基石,塑造了一个效率优先的司法理念,力图使法律服务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淡化了传统法律中的道德与正义范畴。尽管他的某些观点为当代法学界所诟病,他刻薄犀利的写作风格和坚持理性分析的态度,使他的作品成为法律研究和实践中无可替代的宝贵财富。 他的辩证和不合时宜的作风让人们难以将他简单地归类为传统意义上的保守派或自由派。波斯纳本质上是法学界的“异端”大师,敢于质疑前人智慧,勇于推翻权威规范,追求真理的不羁精神贯穿其整个职业生涯。他甚至被称为“保守派的后现代主义者”,这本身就是对传统意识形态的颠覆。
波斯纳的逝去和病痛无疑为他伟大的职业生涯蒙上了悲情色彩,但他留下的学术著作和司法判决仍将持续激励和挑战未来的法律学者和法官。无论赞赏或批评,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位非凡的大师,其思想深度与创造力在人类法律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波斯纳的故事折射出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及其内在复杂性的演变,也提醒我们,法官不仅是法律执行者,也是思想创新者和社会价值的塑造者。 正如波斯纳自己所言,他的创作冲动并非完全源于理性计算,而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表达需求。他是谜一般的人物,也是人类精神的生动写照。无论未来如何评价他,他的贡献已经深深镌刻于法律史册,成为后人探讨法与经济、理性与传统、权威与个性的永恒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