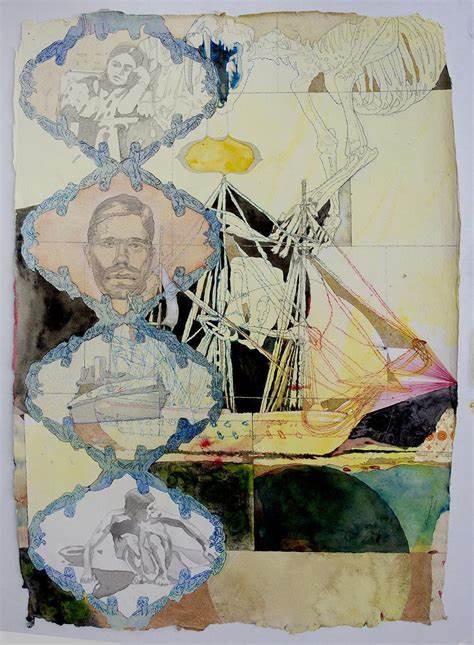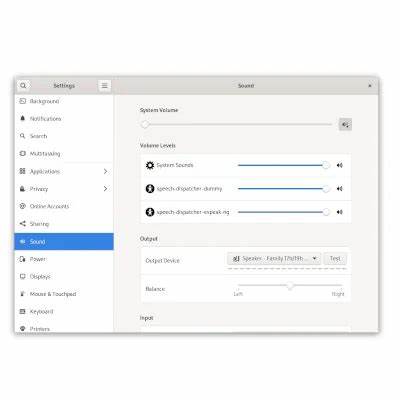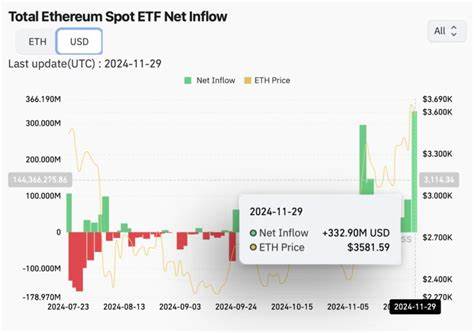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大型语言模型(Large Language Models,简称LLMs)的广泛应用,我们的社会、文化乃至语言交流方式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OpenAI发布ChatGPT后,关于隐私保护、伦理道德、人工智能能否实现通用智能等话题层出不穷,但其中更深层的反思却鲜少被充分关注:人类语言及其交流方式的本质是否正在被这些机器的“语言行为”悄然重塑,甚至削弱? 语言作为人类独有的沟通工具,不仅仅是表达信息的手段,更是建立现实认知、构筑社会信任基础的桥梁。20世纪中叶,心理学家B.F.斯金纳倡导的行为主义认为,所有行为,包括语言行为,都是通过环境中的奖惩机制塑造的。斯金纳在1957年出版的《语言行为》试图解释儿童语言习得过程:儿童通过随机发声得到家长的强化或纠正,逐渐形成语言能力。然而,这一理论受到了诺姆·乔姆斯基的强烈质疑。乔姆斯基提出“刺激贫乏论”,认为儿童语料远不足以支持复杂语言规则的学习,孩子们能够创造前所未有的句子,表明语言习得远超行为主义的简单模拟和强化范式。
尽管乔姆斯基的观点使语言行为主义理论面临重创,硅谷和人工智能研究者们仍将行为主义原则应用于LLMs。不同于限制性且特定环境下的儿童语言输入,LLMs通过互联网海量数据,依据概率模型模仿人类语言,实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语言生成”性能。表面看来,它们通过海量“强化学习”复制了人类交流,但其本质仍是条件反射的产物,没有语言背后的信念、意图和真实世界理解。 实际上,人工智能的语言训练范式与20世纪60到70年代的灵长类动物语言研究如出一辙。当时一些研究者试图通过手语为猩猩等非人灵长类动物赋予语言能力,认为它们由于发声器官限制无法口语表达,手语可能帮助它们跨越这一障碍。例如著名的“大猩猩柯柯”曾在电视节目中展示其手语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然而,研究表明这些灵长类动物的手语表现主要具备工具性,更多地是为了获得“香蕉”等奖励,而非展开真正意义上的分享或创造性交流。猩猩们不会为了表达内心体验或展开关于对象的抽象讨论而使用语言符号,也无法像人类一样灵活组合符号构造新句。 “尼姆猩猩计划”旨在系统验证这些早期声称的非人类语言能力,通过录像和数据整理发现,猩猩的语言使用大多是对训练者行为的模仿反应,缺少主动发起的交流意图。它们的“语言”表达只是表层模仿,并不是认知意义上对世界的分享。这一发现恰恰印证了乔姆斯基关于人类语言独特性的论断:语言并非仅仅是行为的机械复制,而承载着真理探索和共享现实的动机。 而当今大型语言模型正以类似方式“学习”语言。
LLMs通过对海量文本的统计学习,模拟语言的外在形式,生成符合语法规则且表面流畅的文本,但缺乏理解、意图和真诚的沟通目的。它们的语言产出背后是无形的强化机制,旨在满足用户需求、提高文本说服力或者娱乐性,真实世界的认知和真相不在其考量之中。这种“拟人”特征虽然足以应对日常对话和内容生成,但却是“虚假之源”,因为其语言是“华而不实”,仅在表面似是而非,却无法承担语言的根本功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共享理解和真理探求。 社会心理学领域1970年代开展的“说即信”效应研究揭示了语言交流与信念形成的紧密联结。实验表明,当个体为了让对方正确识别某人而进行带有倾向性的描述时,这种交流不仅传递信息,还反过来影响叙述者自身的记忆和认知——他们会内化已验证的语言内容为“事实”。换言之,人类语言交流是一种双向塑造现实和建立信任的过程。
进一步的实验证实,这种效应依赖于语言交流的“真诚”目的,如果参与者意识到交流是为了工具性目的,如获取奖励或取悦自己,这种内化效应则消失。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单纯工具性的互动特质,是追求正确理解和真实共享的社交行为的重要表现。 这正是人类语言与LLMs生成的文本之间的根本差异。非人类机器的语言产出缺乏分享真理、建构现实的动机,而是为工具性目的服务,甚至逐渐改变使用者的交流方式和认知习惯。我们对于“更高效”、“更有影响力”的文本需求,使得LLMs被广泛应用于写作、沟通、演讲等场合,潜在地弱化了真实交流的品质。一旦语言的真诚性被削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便面临崩解,社会联系趋于脆弱,认知真理的能力也将受到挑战。
面对这样的趋势,一些学者提出了数字修道主义的理念,借鉴基督教传统中的贫穷、贞洁和顺从原则,呼吁人们对数字工具特别是LLMs的使用采取自制和节制。贫穷即是减少对数字产品的过度依赖,类似于年轻一代部分人选择“老年机”替代智能手机。贞洁则是拒绝数字及社交媒体带来的心理和伦理污染。顺从强调“聆听”他人而非被技术牵引,保持人与人之间真诚对话的义务与责任。通过这些方式,人类能够有意识地维护语言作为真理交流载体的独特地位,抵御被技术工具异化的风险。 人工智能在医疗、科学研究、编程等领域展现出巨大潜力,为人类创造力提供了有力补充。
然而,当它被用作代替复杂、深刻的人际交流工具时,其负面效应可能深远。语言不仅仅是词汇和句法的堆砌,更是人类共享现实、确立共识的纽带。失去这一纽带,我们便可能走向更加孤立与分裂的社会。 未来的语言生态将如何演进,取决于我们如何把握与人工智能的关系。维持语言的真实性和交流的真诚,将是抵御“虚假之源”蔓延的关键。唯有明确人类语言的独特功能,认识到机器“语言”本质上的仿制性质,才能在数字时代守护我们的共识基础和社会信任。
人在人工智能的洪流中,仍需有意识地建构沟通的深度与广度,切勿沦为技术的附庸,而要成为创造真实交流的主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