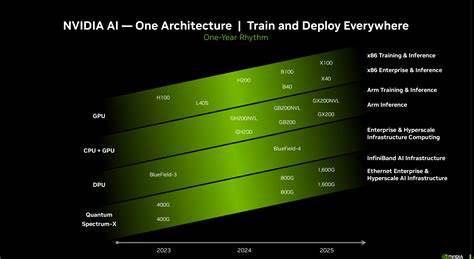政权分赃制度(Spoils System)作为一种政治现象,自古代以来一直是政治权力分配的重要方式之一。在美国历史上,这一制度经历了从总统乔治·华盛顿时期对任职资格的高度重视,到19世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鼓吹的‘胜利者分享战利品’理念,再到20世纪以来因行政国家职能复杂化而逐渐受到限制的演变。然而,进入21世纪,伴随着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和政权政治化现象的加剧,这一制度却迎来了新的挑战与变故。作者罗伯特·马兰托(Robert Maranto)通过亲身经历和深入研究,剖析了后现代主义如何破坏了传统的政权分赃制度,引发了一系列制度性和社会性问题。 回顾政权分赃制度的历史脉络,我们并不难发现,其本质是政治领导人利用任命权,将政府岗位分配给政治支持者,以巩固政治联盟、确保政策执行的忠诚度。19世纪纽约民主党人威廉·马西(William Marcy)所提出的“胜者拥有战利品”名言,充分体现了这一逻辑。
对于当时的政治实践而言,政权分赃制度不仅是一种常态,而且被视为实现政治责任和权利平衡的有效手段。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倡导公务员轮换,旨在防止形成永久的官僚阶层,但是实际上他仅替换了约五分之一的公务员,这说明即使在推崇极端政治任命的时代,权力行使仍受到某种程度的约束。 随着时间推移,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的职能日益复杂,涉及环保、公共教育、性别政策等诸多敏感且技术性强的领域,政治任命的范围与数量显著增加,行政机构也逐渐膨胀。这一时期,政治学家特里·莫伊(Terry Moe)指出,总统利用政治任命作为其直接掌控行政权力的重要手段。随着政治任命越来越频繁地成为政治忠诚度的体现,而不仅仅是能力和专业的象征,制度的平衡开始出现倾斜,政府机构的非政治化和专业化遭遇挑战。 马兰托回忆了自己1990年代在克林顿政府人事管理办公室工作的经历,当时他依然相信,合理运用政权分赃制度可以增强政府效率,并能在下一届政府掌控时得到纠正。
然而,进入2020年代,特朗普和拜登时代的政治氛围反映出旧有的制度约束机制正在失效。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则的质疑与解构,使得政府官员不再因腐败、谎言或绩效差而受到惩罚,而往往因政治忠诚或意识形态立场成为考核标准。这一转变导致政府机构内部权力结构和人事管理更趋政治化,加剧了浪费、欺诈和执行失败,进而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后现代主义在此扮演的角色极具破坏性。它否认客观真理存在的基础,将所有“真理”视为权力话语的产物,从而削弱了科学、法律和传统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监督和知识传递的权威功能。作者指出,诸如批判种族理论(CRT)等左翼后现代主义思想,在高校和新闻机构中占据主导地位,助长了对事实的否认和意识形态标签化。
以哈佛大学前校长克劳丁·盖伊的事件为例,她公开宣称自己“未能传达自己的真相”,而非承认抄袭事实,反映出后现代主义对伦理和客观事实的颠覆性影响。此外,警察改革领域的科学研究成果被政治化审查,阻碍了基于事实的有效政策制定,甚至可能导致更多个体生命的损失。 拜登政府在科研拨款中引入多样性、公平和包容性(DEI)指标及相应顾问聘用要求,也成为科学资助政治化的典型案例。尽管这一做法可能出于推动社会公平的考量,但其实际效果和科学研究的纯粹性却饱受质疑,甚至被认为可能延误癌症等重大医学研究的进展。疫情期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基于种族比例优先接种政策的调整,以及延长学校封闭的决策过程,进一步暴露了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政治干预对公共卫生科学决策的不利影响。这些事件不仅削弱了公众对机构的信任,也加剧了社会撕裂和政策冲突。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也在延续并放大政治任命的范围和深度。新成立的DOGE机构通过迅速裁撤人员,削弱了关键数据收集能力,白宫推行的“第五类公务员”(Schedule F)制度,可能使政治任命数量增加五倍以上,提拔政治忠诚于专业能力和伦理规范之上。马兰托设想,类似将政治口号纳入科研资助资格的做法可能由特朗普政府推进,令科研和行政工作进一步受制于意识形态考量。此种情况下,传统现代政治体系中由新闻媒体、学术界、国会监督权力的平衡已经难以发挥作用。 面对当前体制的动荡,解决之道显得复杂且漫长。短期内,重建公众对政治、新闻和学术机构的信任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长远来看,教育体系的改革尤为关键。强化宪政教育,让年轻一代深刻理解美国宪法的核心价值,诸如言论自由、和平权力交接及国家历史上的重大胜利,将有助于培育理性且具批判精神的公民。正视历史教训,避免极端意识形态对事实的扭曲,是恢复社会共识的基础。 与此同时,建设多元化且科学为本的知识机构,打破当前学术和媒体的单一意识形态壁垒,是实现真理探求和社会问责的重要保障。俄亥俄州设立的萨尔蒙·P·蔡斯公民文化中心等尝试,正是推动包括政治派别在内的内部多元对话的成功典范。类似地,设立专注于第一修正案权利的跨州委员会,也有望成为平衡政治诉求和言论自由的重要举措。
这些机制不仅能够鼓励不同声音共存,避免思想禁锢,也能通过理性讨论遏制极端主义的蔓延。 总之,后现代主义思想对客观真理和法治权威的削弱,加剧了总统任命及政府官僚体系的政治化,破坏了传统政权分赃制度所维护的效率与问责原则。无论是左翼的批判理论,还是右翼的极端民族主义,都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现代民主的根基。通过教育改革、知识机构的重构以及第一修正案权利的捍卫,社会才能逐步恢复理性、多元和信任,摆脱政治化漩涡带来的恶性循环。虽然前路漫长而艰难,但唯有坚持真理与制度的均衡,现代民主政体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内部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