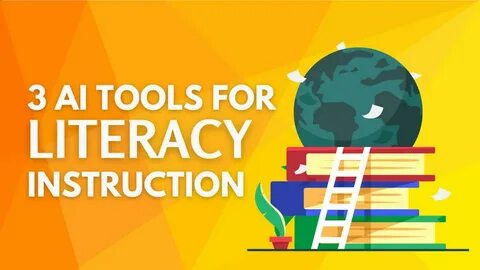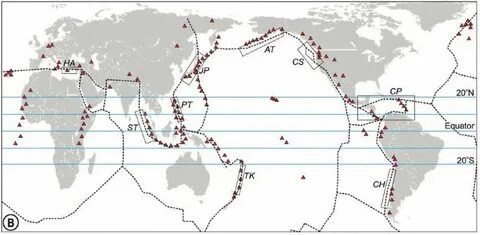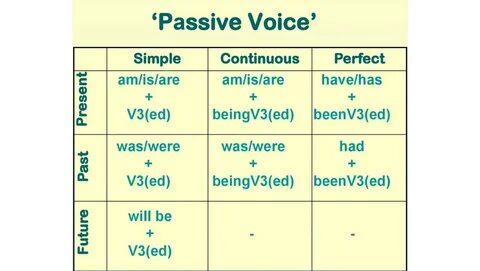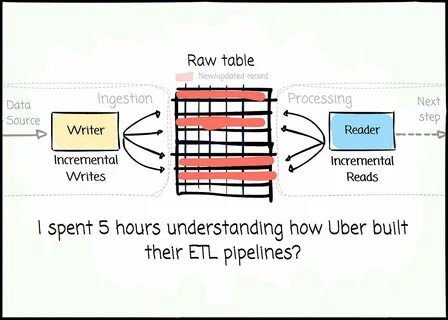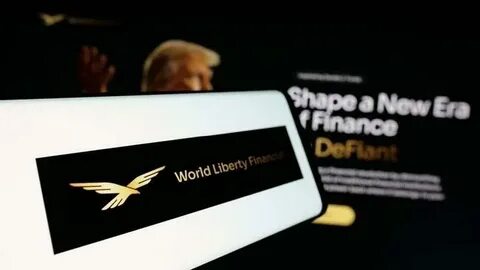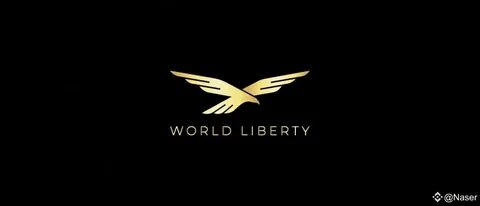近年来,关于识字能力衰退的话题频繁出现在公共讨论中,媒体和学界都在探究为何阅读变得愈发困难,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的冲击下,不论是普通读者还是学生群体,都表现出理解和保持注意力的挑战。识字之所以成为焦虑的源头,不仅因为它是一项基础技能,更因为文字承载着记忆、内心世界乃至自我的认知维度。当识字的生态地位受到威胁,我们感受到的失落远超过单纯的视觉语言处理障碍,而是一种文化认同和内在经验的断裂。识字不仅是一项技能,也不仅是权利或文化遗产,而是复杂且历史依赖的技术体系。它在认知上的作用极为脆弱,需要对其起源、本质及其在脑神经结构中占据的生态位展开深入理解,才能揭示当代面临的威胁根源以及保护它的必要手段。识字的起点并非以个体认知为中心,而是国家机体下的管理工具。
公元前约五千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最早的楔形文字并非为了记录语言音韵或诗歌传承,而是为了协助农耕计划、劳力调配以及社会成员身份的追踪和管理。楔形文字作为表征物,是国家权力合法化、社会秩序统御的符号载体,帮助一个小型管理阶层将庞杂的社会生活数字化、制度化,强化了统治成效,此时文字与国家权力的诞生深度绑定,功能更多是对社会的“上层可见性”而非文化表达。随着时间推移,文字系统经过漫长的改造和社会争取,逐步走向普及,才有了今天普遍认知的“大众识字率”。简化符号系统、普及书写材料、推广教育体系,这些演进都是为了打破早期抄写员精英的垄断,将文字转换成更广泛的认知基础设施。举例来说,字母表系统减少了符号复杂度,使得学习门槛大大降低,促进了识字的普及。但这一过程极其缓慢,从楔形文字时代开始,到现代大众文化基础教育的建立,历经数千年。
这一点提醒我们,任何将权力工具变成认知共享资源的过程,都需要时代的打磨与社会的集体努力。生理和神经学角度显示,识字能力是一项“非自然”的认知创造。人脑并非天生为识字设计,阅读大脑需要重新塑造神经通路,进而克服诸如视觉镜像不变性等先天的视觉习惯。著名神经科学家揭示了阅读需要大脑内分布广泛且资源消耗巨大的网络支持,这不仅说明个体需要长期系统的训练和文化投入,更凸显社会必须持续投入以维持识字生态。然而当前,数字媒体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挑战这一投资生态;新兴的媒介形态往往更符合口头听觉认知偏好,且学习门槛低廉,这使得识字的地位岌岌可危,极有可能退化为一小部分认知精英的专属。人工智能的崛起,使人类社会再度经历一场类似文字诞生的巨大结构性变革,但这次是以数字监控和行为数据为核心。
AI和其庞大的数据生态体系,能够深度追踪、标签化并解读人类行为,其规模和影响力有如古代楔形文字时代的国家管理者,但规模空前且不透明。人类在这套系统面前几乎是被动的:AI阅读我们,而我们难以解读AI,隐喻成“单向镜子”的关系。正如古代文字实现了土地和劳动力的“围垦”,数字时代的AI实现了认知资源的“围垦”,即对注意力、记忆和欲望的封闭控制。经济学界称之为“监控资本主义”,这是新一轮信息的抽取和剥削,围绕着数据、流量和行为的可预测性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识字的深层价值,来自于它对认知能力的递归培养与伦理支撑作用。文字媒介不仅带来信息传递的方便,还促进了同理心、多角度思辨与抽象推理的发展,这些是社会繁荣和个人精神成长的基石。
然而,当我们社会只关注新媒介的表面优势——速度、便利和效率,而忽视了这些“次生效应”,便陷入了短视。现如今,人工智能虽然提供了低门槛、即时查询、语音交互等新功能,但它是否能够培养出类似文字阅读那样深度的人文反思和精神成长,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进一步看,人工智能正意味着“注意力的外部化”,与文字“记忆的外部化”有着深刻的结构对应。写字让我们将记忆从脑内转移到外部媒介,形成公共认知空间和共享记忆。AI则外部化并塑造我们的注意方式,可预测地诱导和重定向我们的焦点与欲望。而此过程的权力初期依旧集中,形成新的认知围垦。
因此,要避免认知共同体被少数权力机构垄断,我们必须重新审视AI的符号架构、治理机制,并将其纳入能够保障权利与公平的公共治理体系中。值得警醒的是,从写字到大众识字的转变用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如今人工智能发展快得让我们无暇等待。如何在短短数年内,指导和塑造AI由集中掌控走向认知共享,实现人类主体的自我强化,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我们不应重复过去的错误,允许认知生态被狭隘私利封锁,而应借鉴历史经验,将AI转化为普及且促进创造力的“心灵匠造工具”。未来社会的认知环境应能保留反思、判断与相互承认的空间,为自由意志和互助提供基础。读写能力的保护已经不仅关乎教育,更关乎政治、伦理和文化的未来。
通过软硬件创新、教育革新及公众参与,建立开放共享的认知工具,共同塑造符合人性需求的新一代信息体系。总之,识字与AI的交汇处,正是人类认知文明面临巨大挑战与机遇的转折点。识字作为文化技术的复杂生态,在人工智能浪潮冲击下摇摇欲坠,呼唤我们用洞察力和审慎来守护其深远的认知价值。同时,人工智能的出现不仅是威胁,也可能成为拓展认知边界和重塑公共认知空间的契机。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我们必须从国家工具的历史中汲取智慧,以开放共享的心态重构数字时代的认知共同体,开启新的“心灵匠造”时代,为未来人类文明注入更加丰富和多元的认知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