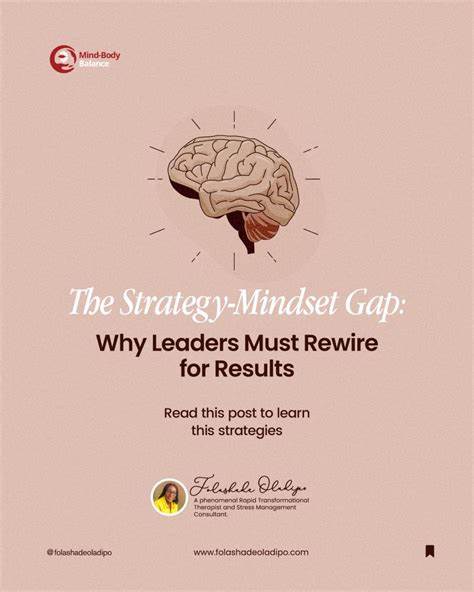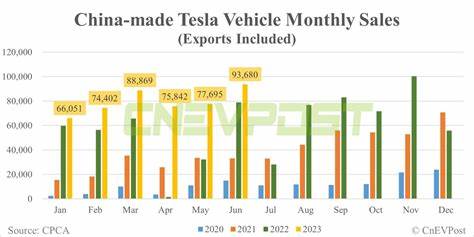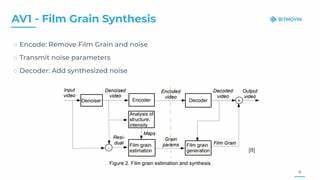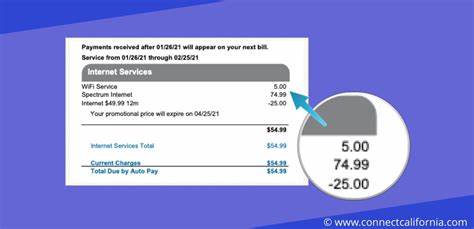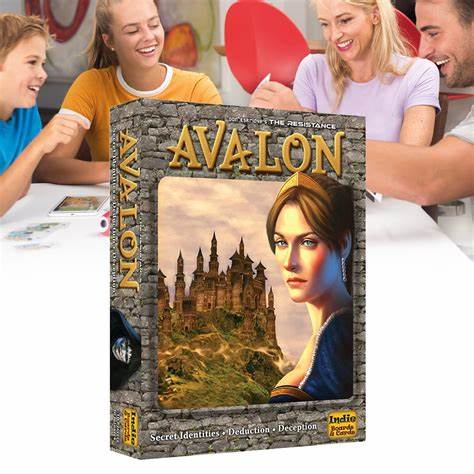弗利特河(River Fleet)作为伦敦最大的地下河流,几乎隐藏在城市的脉络之下,成为很多人鲜为人知的神秘存在。它不仅是一条地理上的水道,更见证了伦敦千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和城市面貌的演变。深入了解弗利特河,可以触摸到一段鲜活的旧时光,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不断发展与革新的脉搏。弗利特河的名字源自古英语“flēot”,意指“潮汐水湾”,这一词根反映了河流与潮汐及航运的紧密关联。在古代,弗利特河曾是一条重要的河流和泊船港口,连接着伦敦的内陆和泰晤士河。河流的下游段也被称为Holbourne(或Oldbourne),这一名称则是伦敦地名“Holborn”的由来。
弗利特河的影响可以在城市的多个地名中看到,如举世闻名的弗利特街(Fleet Street),其东端即从原先的弗利特桥(Fleet Bridge)起始,经过现今的勒德盖特广场(Ludgate Circus)直至泰晤士河边。虽然弗利特河如今已全面被地下涵洞和下水道所覆盖,但依然可以通过城市地形的起伏和某些遗留物迹察觉其存在。在伦敦的北部区域,弗利特河的源头始于汉普斯特德荒野上的两股水流,这两处源头曾被18世纪修筑的汉普斯特德水池及哈伊盖特水池所拦截。之后水流蜿蜒进入地下,穿过坎顿镇,最终汇合成一条河道。整个河道长约六公里,沿途经过肯蒂什镇(Kentish Town)、圣潘克拉斯老教堂(St Pancras Old Church)等地,河流的自然曲折塑造了今天国王十字车站(King's Cross)及其周边建筑的独特布局。例如德国体育馆及大北方酒店都顺应河流的弧线而建,充分体现了水路对城市规划的深远影响。
国王十字地区旧名“Battle Bridge”起源于河流上的一座宽阔浅渡口“Broad Ford Bridge”,体现了历史与地理的交织。一些历史学者甚至将这里与著名的罗马女王布狄卡的终战之地联系起来,尽管相关证据并不确凿。从圣潘克拉斯老教堂往南,弗利特河沿着现代的国王十字路及法灵顿街(Farringdon Street)延伸,并形成克莱肯维尔(Clerkenwell)、霍尔本(Holborn)及圣潘克拉斯三个区的界限。河道的谷地形态依旧影响着周边街道的地理走向,尤其是Holborn高架桥(Holborn Viaduct)、Shoe Lane及Rosebery大道处三座高架桥的存在,正是为跨越古老河谷而建。弗利特河的一个著名支流是兰姆汇水道(Lamb's Conduit),它曾经是一条从西向东流入弗利特河的小溪。煤气灯时代的伦敦人曾依赖这条汇水道提供清洁水源,尽管最终它也被纳入地下排水系统。
另一个重要支流是法格斯韦尔支流(Fagswell Brook),这条汇入弗利特河的支流曾作为伦敦城的北界。十六世纪早期,历史学家约翰·斯托(John Stow)曾记录了该支流被阻塞的情形,反映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早期演变。现代伦敦已将弗利特河完全纳入下水道系统,水流经过贝克顿污水处理厂进行净化处理。尽管弗利特河早已“入土为安”,但在克莱肯维尔的Ray街、华纳街等地,仍然可以听到流水流淌的声音,雨季时甚至可见隐约的水流映现于路面格栅下。在泰晤士河畔,靠近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下方的河口处,潮水涨落时,污水溢出管口所形成的水流正是弗利特河的最后出口。伦敦前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曾提出“复兴伦敦失落河流”的计划,意欲将弗利特河部分地段重新开放为城市的观赏水体,赋予城市河流新的生命和文化意义。
但环境署对此持谨慎态度,认为弗利特河卫生条件恶劣,要实现清澈见水的复兴困难重重。弗利特河的历史渊源可追溯至罗马时期,当时河口可能建有世界上最早的潮汐水车,这一工程体现了古罗马人在水利技术方面的先进水平。河流不仅护卫了伦敦古城的西侧,还为古城居民提供了珍贵水资源。到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弗利特河仍是宽广的水道,河口区域有宽达百余米的潮汐沼泽区,丰富的水资源孕育了许多被认为具有疗效的泉水,如巴格尼吉水井和圣布莱兹水井等,吸引了众多信众前来沐浴祈福。随着伦敦城市的扩张,弗利特河的水质逐渐恶化,成为了排放污物的暗渠。其周边地区因环境恶劣而聚集了贫民区及多座监狱,包括著名的布赖德韦尔宫监狱、新门监狱、弗利特监狱和勒德盖特监狱。
十八世纪,著名诗人亚历山大·蒲柏在其讽刺长诗《愚人颂》中曾描写弗利特河及其水质的污染情况,抨击其作为“污泥之王”的恶名。17世纪大火后,建筑师克里斯托弗·雷恩曾巨资提议扩宽弗利特河以改善城市水道,但这一计划最终未被采纳。1680年,在科学家罗伯特·胡克的监督下,弗利特河被改造为“新运河”,部分河段沿线发展成煤炭码头,便利了当时伦敦南北的煤炭运输。18世纪30年代以后,上游河段封闭改建成“弗利特市场”,而下游河段则先后被覆盖,建设了多个道路和桥梁,逐步彻底隐藏在现代都市之下。19世纪随着摄政运河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兴建,弗利特河流经国王十字、坎顿等地段相继被覆盖。弗利特河的发展轨迹也被当时的艺术家兼历史学家安东尼·克罗斯比详细记录,他的草图和笔记如今珍藏于伦敦档案馆的克罗斯比收藏,为后人研究这条“隐形河流”的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弗利特河不仅塑造了伦敦的地理格局,也深入融入了文学艺术作品之中。多位英格兰文学大师如本·琼森、乔纳森·斯威夫特和查尔斯·狄更斯都曾以弗利特河为背景,创作出描绘城市污水系统讽刺与现实的作品。狄更斯的《雾都孤儿》中特别提及弗利特河邻近的繁华与贫困,赋予了这条河流独特的文学象征意义。现代文化作品中,弗利特河的形象依旧鲜活。电影《福尔摩斯》曾在场景设定中引用了弗利特河的地形标志;科幻电视剧《神秘博士》、小说《伦敦河》以及尼尔·盖曼的《伦敦地下》等作品中,也多次出现这条地下河,充满神秘色彩与传说。当代诗人保罗·奥普瑞更通过现代诗歌,沿着弗利特河的水路,呈现其隐藏于现代城市中的自然美与历史沉淀。
弗利特河的故事代表了伦敦这座城市如何与其自然环境共生共存,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既保护又改造自然资源。它既是历史的遗迹,也是现代生态和环境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更多关于地下河流恢复和环境整治的讨论,激起人们对弗利特河未来的期待。它或许不会恢复昔日清澈的水质,但作为伦敦地下网络的一部分,依然体现着城市与自然的交织与共鸣。弗利特河,犹如伦敦深藏的动脉,默默流淌于钢筋水泥之下,连接着过去与现在,见证着一座世界名城的变迁与创新。从昔日作为港口和生活水源,到被逐渐掩盖为城市的排水系统,这条地下河流无疑是伦敦不可或缺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象征。
探寻弗利特河,是一场穿越时空,理解伦敦这座多层次城市的独特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