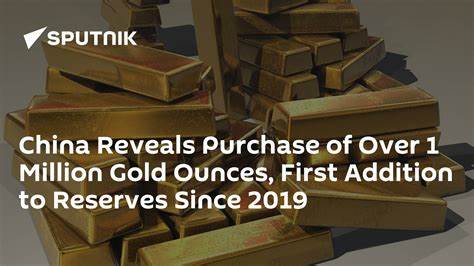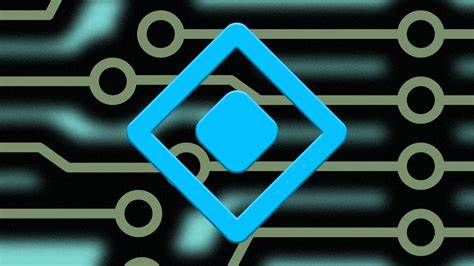伊朗曾经怀揣着宏大的帝国梦想,试图将叙利亚打造成为其经济及政治影响力的延伸地。它的计划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军事或政治干涉,而是一场借鉴美国“马歇尔计划”模式的大规模重建行动。通过投资数十亿美元,伊朗试图帮助叙利亚摆脱内战的废墟,从而加深对这个中东关键国家的控制与依赖。然而,随着阿萨德政权的垮台,这一切终被现实撕碎,伊朗的野心也随之破灭。 伊朗的“马歇尔计划”蓝图由驻叙利亚的一支经济政策单位于2022年5月完成,文件以一份长达三十三页的研究报告形式出现。在这份文献中,伊朗明确提到了二战后美国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并称其成功之处在于实现了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层面的依附关系。
伊朗希望通过类似策略,将叙利亚改造成一个“经济帝国”,巩固对其盟友巴沙尔·阿萨德的影响力,并借机扩大其在中东的战略纵深。 这项宏大的计划不仅包含了重建基础设施,更延伸至矿产资源开发、农业产业化、能源项目以及高科技电信领域。为此,伊朗派出了大量工程师和企业团队,积极承接涉及发电厂、铁路桥梁、油气项目等多个关键工程。比如,在叙利亚沿海城市拉塔基亚,一座价值逾4亿欧元的电厂项目被伊朗企业承包,但最终未能投入使用。类似的油田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因战争影响、当地腐败以及西方制裁受阻。尽管投资规模巨大,却鲜有实质性回报。
巴沙尔·阿萨德在2024年12月被叛军推翻标志着伊朗计划破产的关键节点。阿萨德政权的倒台使得伊朗支持的武装及民间企业纷纷撤离叙利亚,伊朗在当地的外交机构被洗劫一空,数以千计重要文件散落地面。新上任的亲叛军政府,主要由曾反对伊朗的组织哈亚特·塔赫里尔·沙姆(HTS)领导,对于承认和偿还叙利亚对伊朗产生的数十亿美元债务表现出极大不情愿。 HTS的新政权重新塑造了叙利亚的政治版图,他们宣称希望打造一个包容且民主的国家,但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与安全风险。对于曾与伊朗紧密合作的叙利亚企业家和劳动力而言,伊朗撤离造成了生计严重受损。许多企业主因伊朗贷款和合同的中断而蒙受巨额损失,曾经依赖伊朗经济支持的工人则陷入失业和流离状态。
伊朗的经济投资最早于2008年启动,通过像马普纳集团这样的基础设施企业,先后获得了多个发电厂扩建及电网修复合同。在战争前夕,伊朗和叙利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提供了大额信贷支持,用以促进双边贸易以及支持叙利亚政府的进口需求。然而,随着叙利亚内战爆发,局面迅速恶化,安全风险陡增,外国企业纷纷撤退,伊朗对此依然紧咬不放。叙利亚的动乱导致库房被抢占,货物被劫持,资金迟迟未能到账,更被本地腐败案件和复杂的官僚体系拖累,投资项目不断延期甚至停摆。 西方国家针对伊朗及叙利亚的严厉制裁更是将局势推向了绝境。尤其是美方的空袭严重破坏了关键基础设施,包括由伊朗资助建造的铁路桥梁。
虽然伊朗内部依然努力推动与叙利亚的经济合作,试图通过设立联合银行、零关税贸易以及本币交易避免美元管制,但效果甚微。与此同时,叙利亚也开始寻求与俄罗斯、土耳其以及若干阿拉伯国家修复关系,试图为其磕磕绊绊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经济领域,伊朗在叙利亚的军事和文化影响同样深远。伊朗支持的准军事组织遍及大马士革、赛义达·扎伊纳布和阿勒颇等战略地区,控制着武装力量和民兵训练。宗教领域伊朗维持着重要的什叶派圣地赛义达·扎伊纳布清真寺的维护和资助,每年有数十万信徒前往朝圣。这种宗教纽带是伊朗与叙利亚深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伊朗在当地赢得一定的软实力支持。
尽管如此,普通叙利亚民众对伊朗的印象却极为复杂,许多人认为伊朗的介入加剧了该地区的纷争与创伤。 伊朗试图将叙利亚打造成为“卫星国家”,寄望于经济依赖实现政治控制的梦想,无疑是一场代价惨重的赌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叙利亚市场被安全威胁、国际孤立及内部腐败所阻隔,而阿萨德政权的崩溃更为这场计划画上句号。过去的几年里,伊朗不仅未能收回其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投入,反而面临来自区域对手土耳其和以色列的竞争压力。 未来叙利亚的重建道路漫长且充满变数。新政府面对越来越多的被冻结的基础设施项目与资金缺口,如何重建国内经济生态成为当务之急。
伊朗的军事撤退以及经济影响力的衰落,意味着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也在持续演变。尽管伊朗仍然保持一定的地区影响力,但其试图复制美国“马歇尔计划”式的模式在叙利亚未能成功,也凸显出地区和国际环境的错综复杂。 伊朗的经验亦为国际社会以及其他国家敲响警钟。对一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进行大规模复兴和经济注资,必须充分考虑安全保障、政治稳定、国际制约及当地社会结构等多重因素。投资风险巨大,任何单一外部力量的长期主导尝试都可能因政治局势突变而中断甚至失败。总的来说,伊朗在叙利亚的帝国梦终究未能成真,其失败背后折射出的是在现代国际博弈中,单靠经济投入难以实现政治控制的深刻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