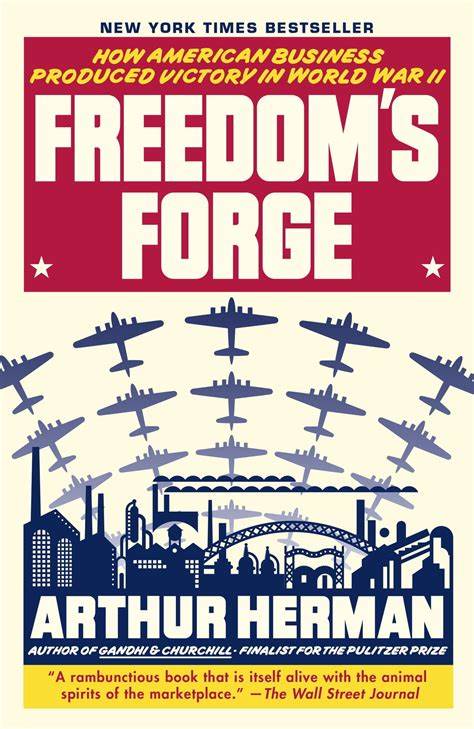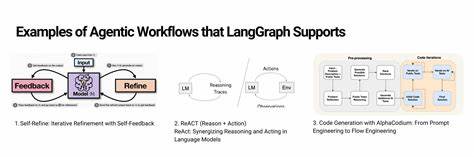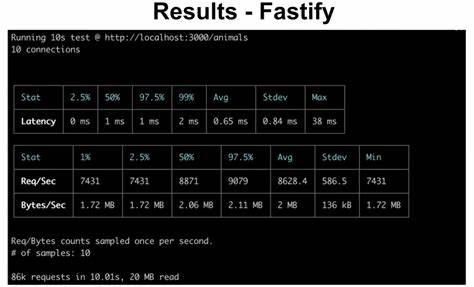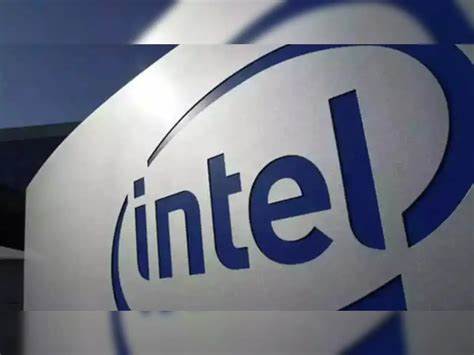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尤其是在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博弈愈发引人关注。历史往往是最好的老师,回顾二战期间美国所采取的工业动员策略,可为当下AI领域的竞争提供宝贵的经验。二战初期,美国政府在极短时间内将国家经济转向战争生产,实现了飞机、军舰和装备的快速工业化生产,成功塑造了“民主的军火库”。如何将这一模式应用于当代的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美国20世纪工业动员的核心在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时任汽车行业高管比尔·克努森被赋予领导国家制造转型的重任,他深刻认识到企业利润驱动的重要性,强调“必须让企业从中获利,否则企业不会有效运作”。
政府通过成本加固定利润的合同模式,向民用承包商预付巨额资金,确保他们无忧地扩建工厂、研发技术、培训人力。正是这种强有力的资本支持,激发了工业界的创新与扩张,使美国工厂在战争期间生产了约三分之二的盟军军事装备。与今天AI领域主要依赖风险投资的模式不同,二战时期的资金注入侧重于战略目标而非短期财务回报。在战争紧急状态下,速度成为制胜关键。政府不拘泥于繁琐的手续,宁愿用简短的计划书快速推动落实。例如在1942年,海军长官维克里仅用一句“周一开始”便批准凯泽船厂的三页简要方案,催生了极具创新和规模效益的快速造船技术。
这种对试错和快速迭代的容忍,加上坚定的政府支持,使得凯泽的船厂仅用一年多便能将建造一艘完整货船的时间缩短到仅四天。相较之下,现代社会科技项目常常被繁文缛节拖延,缺乏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速度意识。二战的动员模式还充分注重打造产业生态系统。以福特汽车公司在威洛伦工厂生产B-24轰炸机为例,福特不仅自身投入巨大,也带动了数百家供应商协同合作,形成涵盖零部件制造、组装与物流的完整产业链。这种分布式但紧密协作的供应体系培养了大量新业务与技能人才,同时为战后美国经济的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相反,现代的人工智能发展更多聚焦于单一企业或初创团队,缺少国家层面的系统性生态建设。
当前,世界正处于一场类似于二战工业竞赛的AI竞赛中,科技的未来走向关系重大。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规模扩张上发力,试图复制美国军事动员的紧迫感和规模效应。而美国在AI领域依赖更多的是私营风险投资,虽然对创新有积极推动作用,但面对战略竞赛所需的快速工业化建设,现有模式存在短板。以半导体制造为例,先进芯片的制造依赖极紫外光刻机(EUV)这一稀缺装备,全球唯一厂商荷兰ASML的高端产品价格高达3.8亿美元一台,这使得相关设备的制造和产业链建设难度极大。借鉴历史经验,美国政府可考虑向半导体制造提供成本加固定利润的政府合同,支持包括英特尔、台积电及潜在新入局者在内的多家企业建设高数值孔径EUV设施,形成多点布局和高强度资本保障。通过打造基础设施和生态系统,巩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战略地位。
尽管二战成本加合同模式曾招致过部分浪费的批评,例如臭名昭著的“六百美元马桶座”,但相较于其所创造的巨大价值,浪费显得微不足道。正是这种体制下的强力投入和宽容失败态度,推动了喷气发动机、雷达、合成橡胶和抗生素等多项关键技术的诞生。今天的科技竞争也需要类似的勇气与坚定,承认在高风险高投入的前线研发过程中,短期效率和成本控制不可过于苛求。此外,像B-29超级堡垒轰炸机项目这样规模庞大、技术复杂且回报周期长的国家战略项目,在缺乏政府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私人资本难以承担高风险。B-29的众多创新技术在战后仍广泛应用于航空工业,证实了战略投资的远见。回顾历史,二战美国工业的成功依赖于政府的战略远见与私营企业的执行力相结合。
构建“民主的军火库”不仅是政府单方面的注资,更是与产业界深度合作的结晶。当前全球进入新一轮大国技术竞争时代,人工智能的未来不仅取决于创新能力,也取决于能否形成有效的“生产力体系”。吸收历史经验,美国若能结合风险资本的创业活力与政府的战略投资力量,将有望打造出领先全球的AI产业生态,确保国家的科技领导地位延续至21世纪。正如历史所展示,战略竞争不仅需要智慧的技术创新,更需要有力的资本投入、速度意识及产业链系统建设。塑造未来科技优势的关键,是政府与企业携手合作,共同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将历史经验转化为现代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