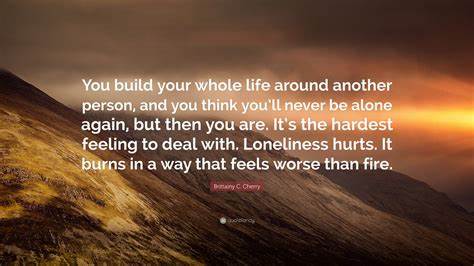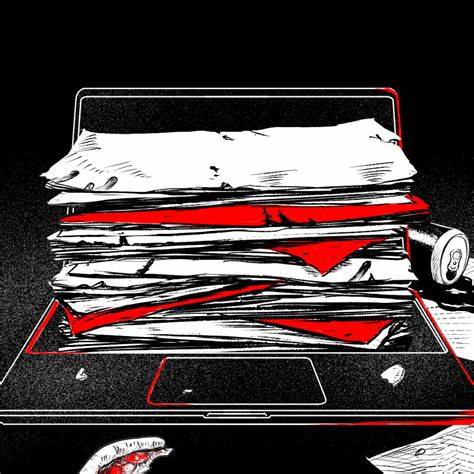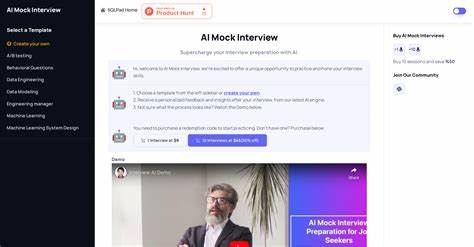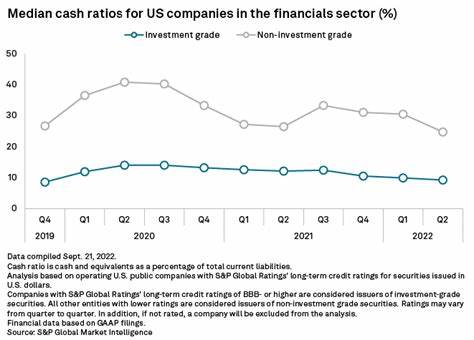在现代政治舞台上,权力的滥用和独裁倾向并非罕见,但近日美国围绕特朗普总统及其政策的讨论中,预期性顺从(anticipatory compliance)这一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所谓预期性顺从,指的是美国的大学、企业、媒体乃至司法机构在特朗普未正式提出要求之前,主动迎合其意志、调整自身行为,以期避免惩罚或获得政策上的青睐。然而这种做法不仅助长了权力的扩张,更成为民主制度和法治基础的隐患。面对这一挑战,提出并推行预期性拒从(anticipatory noncompliance)的战略,成为维护美国社会多元自由和制度独立的关键所在。特朗普任职初期,以推翻传统政治秩序、重塑美国形象为目标,迅速展开政策攻势。然而社会各方的过度谨慎和提前顺从,给他的权力扩张开了绿灯。
高校在面对其以反对所谓“意识形态”课程为由威胁削减联邦资金时,纷纷自我审查,删除课程中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关键术语。公共教育系统为避免资金缩水,被迫调整历史教学内容,甚至限制学生阅读重要文学作品如托尼·莫里森和罗莎·帕克斯的作品。这种迎合行为极大削弱了教育的自由与完整性。媒体方面,为了避免被特朗普起诉或成为其攻击目标,大型传媒集团缴纳巨额和解费用,或选择取消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支持。影响力巨大的《华盛顿邮报》也曾因其老板杰夫·贝佐斯的商业利益考虑,在2024年大选前撤销了对卡马拉·哈里斯的支持声明。这种先发制人的顺从无疑削弱了新闻自由,破坏了舆论独立。
在法律领域,面对总统行政命令的严厉打压,九家顶级律师事务所被逼放弃为反对者提供公益法律援助,并转而承担特朗普指定的辩护任务,这种自我阉割削减了法律援助的广度和深度,妨碍了法律监督的正常运行。此外,包括亚马逊和百事等跨国企业为了避免成为社交媒体攻击的焦点,主动取消或缩减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性(DEI)计划。这不仅丧失了企业内在的社会责任感,也忽视了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对多样性的认可和支持。所有这些预期性顺从的行为背后,是机构因恐惧和利益计算而作出的策略选择,却无形中助长了专制势力的膨胀。尽管屈服似乎是一种短期的“明智”行为,长远来看却为极权统治铺平了道路。历史经验表明,专制者对忠诚和让步的需求永无止境,预期性顺从只会激励其不断加码,侵蚀制度和公民权利的防线。
面对这种情势,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倡导预期性拒从,积极抵制提前降服的诱惑。在学术界,哈佛大学率先表态,坚决反对政府的过度干预。包括“十大学术联盟”在内的多个高校通过联合防御协定,明确划定拒绝妥协的红线,实现了集体发声和行动的力量。多达数百名高校管理者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只有共同对抗政府的政治干预,才能保护美国高等教育的学术自由。此外,19个州的政府也选择通过法律途径挑战行政部门在民权法的曲解使用,抵制公共教育领域的“白化”和课程审查。企业界的反弹同样令人振奋。
曾因缩减DEI导致消费者抵制和股价暴跌的目标公司案例警醒了众多企业,苹果和好市多等坚持多样性承诺的公司赢得了市场和投资者的认可。微软结束对退让事务所的合作,转而支持法律界对抗特朗普政府的行动,体现了商业与道义的双重胜利。法律界中,多家领先律所拒绝屈服,采取上诉和诉讼手段保护公平正义。美国司法系统也表现出强劲的独立性,许多法院坚决维护法治底线,驳回了政府涉及权力扩张的多项行政命令。民众层面,经过初期的沉默和恐惧,广泛的反抗与示威活动陆续兴起。2025年5月1日的“五月劳动节”当天,全国各地爆发了近千场反特朗普集会,成千上万的公民走上街头,高喊对专制的拒绝。
这种激烈的社会参与预示着民主精神的回归与觉醒。恢复和保护民主并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持久的斗争与多样的行动手段。诉讼、示威、消费者抵制、政治动员等多重策略组合,形成对抗权力滥用的坚实防线。虽然过程充满艰难和挑战,但正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不是所有面对的事情都能被改变,但只有面对它,才有改变的可能。”如今美国社会的积极回应给人以希望,显示出公民和机构愿意为自由和公正展开艰苦奋斗。总而言之,预期性顺从是当代政治中的严重陷阱,它助长了权力的独断与专横,削弱了制度的坚韧和社会的多元活力。
唯有通过预期性拒从,拒绝在权力面前低头,机构和民众才能守护民主的根基,防止权力的无限扩张。美国社会当前的种种反抗行动和法律挑战,不仅为维护法治和自由树立了榜样,也为全球民主阵营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启示。面对任何形式的权威压迫,勇敢说“不”,是每一个公民和组织责无旁贷的责任。坚持抗争,直面挑战,民主的光芒必将得以延续和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