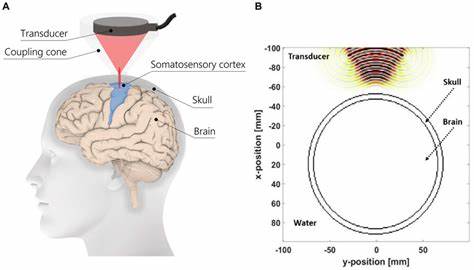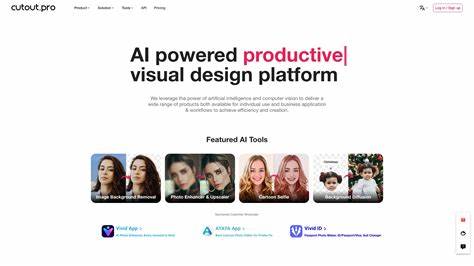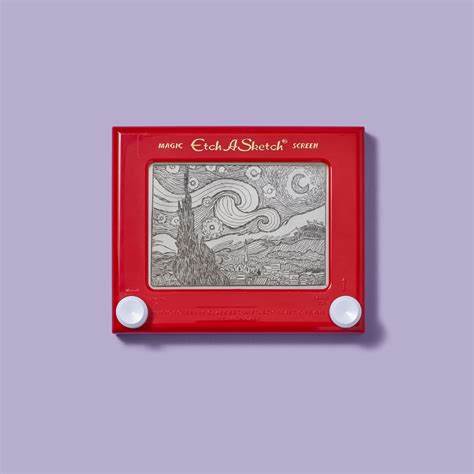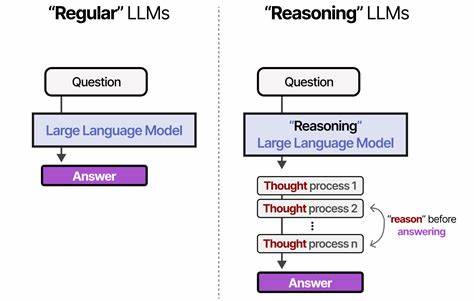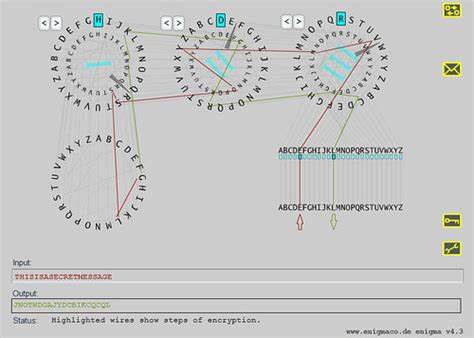近年来,二次方筹资(Quadratic Funding,简称QF)作为资助公共物品的创新机制,在Web3领域引起了广泛关注。以Gitcoin的资助项目为例,截至2024年1月,利用二次方筹资机制已分配超过5900万美元的资金。然而,尽管二次方筹资以其理论上的最优性令人心动,但事实上,它离真正的最优资助机制还有不少距离。其背后的各项假设往往在现实中难以成立,导致该机制在实际操作中面临诸多挑战。深入剖析这些前提条件,才能更好地理解二次方筹资局限所在,并为未来公共物品资助机制的改进提供启示。首先,财富平等是假设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理论上,二次方筹资假设人民财富分布均匀,因此更大的捐款意味着更高的边际效用。然而现实社会中,收入和财富差距极大,富人和穷人在贡献公共物品资金的能力及意愿上有明显差异。举例来说,十位富有的艺术赞助人各捐赠一百万欧元,合计一千万欧元,根据公式,二次方筹资将为该艺术项目匹配高达一亿欧元的补贴。而十位低收入者每人捐赠一百欧元,总额仅一千欧元,但依此计算会获得一万欧元的补贴,资金投入与社会效益之间存在明显的错配。结果导致资源更多地流向具备高支付能力的群体,可能无意中加剧财富再分配的不公平,背离了公共物品资助的初衷。其次,免费补贴的假设也极具争议。
二次方筹资的理论最优性依赖于补贴部分是无偿的,即补贴资金不会给资助者带来成本。然而实际运作中,这些补贴往往来源于税收或者牺牲其他社会资源的机会成本,间接由公众负担。当富裕群体享受了更大补贴,普通纳税人则可能承担更大的负担,造成财富从弱势群体向强势群体的转移。这样的补贴设计不仅损害社会公平,也可能激发公众的抵触情绪,阻碍机制的持续运转。利己贡献者的行为假设也是二次方筹资最优化背后的关键条件。理想状态下,所有贡献者都是完全利己的,直接体验到贡献带来的个人效用。
若贡献者出于纯粹利他主义,未能直接获得效用,则可能导致项目过度资助,反而降低整体社会福利。例如三位艺术赞助人各捐赠一百万欧元,其获得的个人享受带来高额边际效用,社会整体产生正向福利增益。对比于三家慈善组织向癌症研究捐赠同等资金,因效用仅由受益患者体验,三家机构自身并无直接效用,结果反而在资金与实际效益间出现负面差距,社會福利净值下降。这显示若贡献动力非以个人效用为准,则二次方筹资效力大打折扣。关于均衡发现的问题,二次方筹资要求贡献者能预测其他人的资助水平,据此调整个人出资达到纳什均衡。然而现实中,贡献者缺乏完备信息,难以准确洞悉他人的投入,因此难以理性决策。
缺乏良好均衡发现机制将导致资助活动充满猜测,结果难以实现理论最优。在多项目资助时,某项目突然吸引大量关注可能导致许多人误判最终均衡,形成资源错配和浪费。此外,项目资助预算必须足够大以覆盖理论上的资助缺口。若组织者预算有限,无法承担所有项目的匹配资金,将不得不选择多重均衡之一,造成资助效率与社会福利的下降。资本有限情况下,虽然可以采用资本约束式二次方筹资,但本质仍因资金不足而导致机制性能下降,最优性丧失。另一个核心假设是贡献者对项目拥有完美知识,包括所有项目的信息及贡献情况。
现实世界中项目公告有限,宣传不充分或者项目本身复杂,使得贡献者难以对所有潜在资助对象作出理性且全面的评估。那些善于造势和营销的项目往往占据优势,吸引更多赞助,忽视了潜在效率更高但知名度较低的项目。资助资源配置因此受到信息不对称的严重扰动。关于贡献者必须独立行动也是假设中不可忽视的部分。二次方筹资假定没有协同作弊、虚假身份或串通行为存在,否则便可能爆发财务欺诈和资源被盗用的风险。事实上,Sybil攻击和贿赂策略已在多个平台频繁出现,严重威胁机制的公正性和有效性。
尽管已有研究和实践尝试引入防串通和防伪造改进措施,如连接导向的集群匹配方法,但这类改进通常牺牲了机制的单一均衡和理论最优性,使实际操作更复杂且难以把控。整体来看,二次方筹资尽管在理论层面展示了令人艳羡的最优资助分配功能,但其背后的八大核心假设——财富平等、免费补贴、利己贡献者、均衡发现、充分预算、递减边际效用、完美知识与贡献者独立——在现实多半难以同时满足。缺乏这些条件,二次方筹资结果往往远离理想,甚至带来逆向效果,如资源错配、财富再分配逆转及资金浪费。当前学界和实践界正积极探索针对这些不足的改进途径,尤其是在防止协作作弊和负面外部性方面取得一些进展。然而,如何兼顾公平、效率和激励机制的稳定运行,仍然是公共物品资助领域亟待解决的核心问题。从更广阔的公共资助视角出发,可能存在或将涌现出比纯粹二次方筹资更适应现实条件的资助机制。
理解二次方筹资的不足,有助于研究者和实践者制定更加灵活且公平的公共物品资助方案,推动社会资源朝向最大化的社会福利分配。未来的公共物品资助机制,势必要在激励兼容、信息透明、抗作弊与社会公平等多个维度取得平衡。只有跳出单一理想模型,结合多元化手段和实际环境限制,才能真正实现公共资源高效且公平的筹资与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