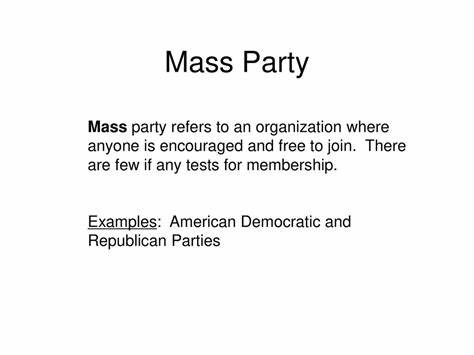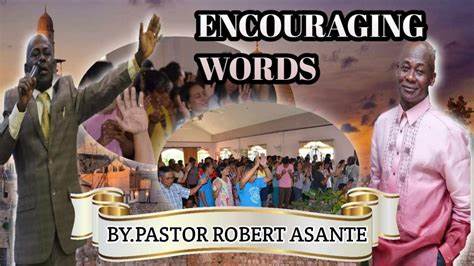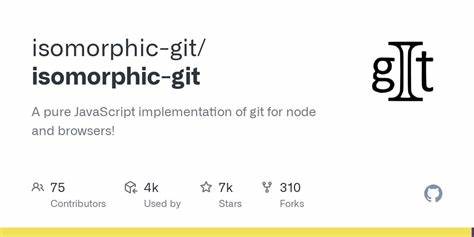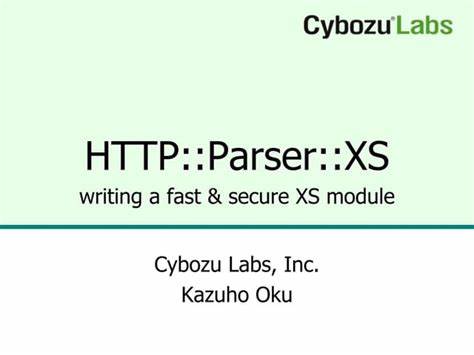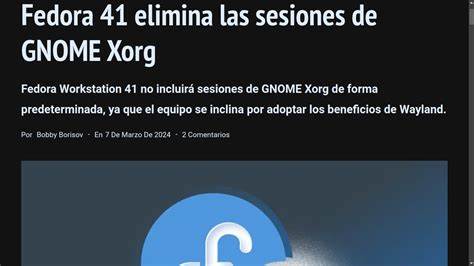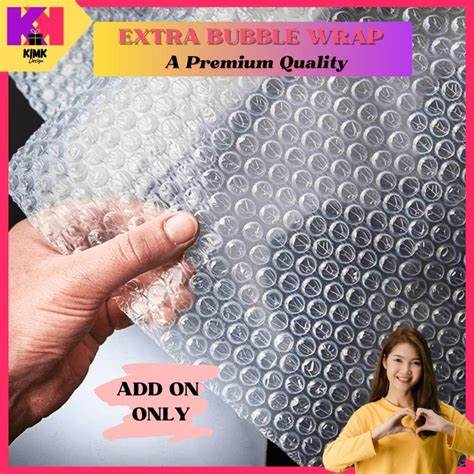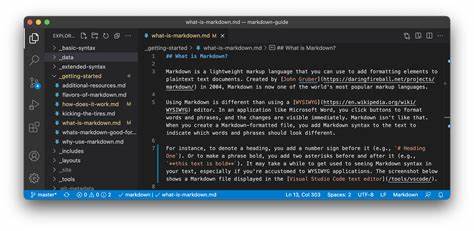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全球政治生态的快速变迁,传统意义上的大规模会员制政党逐渐走向边缘化,取而代之的则是以咨询机构、利益集团及短期战略为核心的专业化、精英化政党运作模式。学者们普遍认为,这种转型导致了民主中介的缺失,削弱了政党与普通公民之间的联系,加剧了政治极化与民众对政党的厌恶,甚至威胁着民主制度的稳定。著名政治学家Didi Kuo在其著作《大撤退:政党衰败如何破坏美国民主》中深入剖析了这种现象,提出了政党重建的必要性及可能路径,引发了学界和实践界的广泛关注。历史上,政党是社会中各种集体力量与公民团体的结合体。二十世纪中叶,政党往往扎根于劳动组织、宗教团体、地方社区,承担着连接公民与国家的桥梁功能。它们不仅参与选举,更持续参与社区生活,与选民建立长期的情感纽带和政治认同。
例如,美国早期的机器政治时代,政党通过深入了解选民的需求与期望,在地方层面实现了高度的动员和服务,成为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石。这种模式的政党在经济领域也发挥了关键角色。特别是社会民主和工人阶级政党,它们致力于通过集体谈判、社会保障体系和经济规划,调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矛盾,为广大劳动者争取权益,同时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表明,强大的政党不仅是政治竞争的工具,更是社会公平和经济正义的推动者。进入20世纪末,尤其是在美国和欧洲,政党的结构和功能经历了深刻变化。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的兴起,许多传统左翼政党开始调整其立场,转向市场导向的政策,淡化经济改革,试图在选民中寻求更广泛的支持。
这种转型导致了政党核心支持群体的丧失,也使得政党变得日渐依赖专业咨询团队、外部捐助者和广告宣传,而非扎实的基层组织和会员参与。结果,政党变得更加短期主义和以选举为中心,缺乏持久的社区存在,政治身份认同也趋于碎片化。同时,这种现象也导致了经济利益被忽略的空间被极右翼民粹主义者填补,激发了基于文化焦虑和身份政治的竞选策略。面对这一局面,政党的再建成为民主发展的关键议题。Didi Kuo认为,要扭转这一趋势,必须重塑政党作为社会中介机构的角色,恢复其与基层的深度联系和持续参与。这不仅需要中央层面对竞选资金的集中管理,限制外部利益集团的影响,还要重视地方组织建设,激发普通党员的积极参与,使政党真正成为代表群众利益、反映核心选民诉求的平台。
部分欧洲政党的成功经验为此提供了启示。例如,一些党派通过提供参与政策制定的机会、组织社会活动和提升党内领导的透明度,有效增强了会员的归属感和凝聚力。墨西哥的莫雷纳党则采取了创新措施,通过随机选拔党员作为候选人,提升了代表性与选民认同。这些做法虽然不能完全回归以往依赖强大劳工运动和公民社会支撑的模式,但显示了政党在新条件下的适应和再生可能性。然而,现实挑战依然严峻。过去催生大规模会员制政党的社会经济环境已难以复制。
工业化带来的庞大工业劳工阶级和发达的协会组织体系普遍衰落,信息时代的个体主义和社交媒体塑造了分散且短暂的政治参与模式,弱化了传统的群体认同。同时,资金驱动的竞选机制使得政党更易受制于利益寻租,基层动员成本高企。这意味着,单纯模仿历史模式的复兴难度极大。面对复杂现实,重建政党需要创新思维。部分行动者开始尝试逆转政党与社会关系的传统模式,不再被动依赖强大的社会机构作为支撑,而是在社区层面主动创造新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纽带。例如,美国农村和低收入地区的“城乡桥梁计划”通过非党派的公益活动,逐步建立民主党在基层的正面形象和持续存在感。
这类项目虽非直接政治动员,但为未来的政治参与奠定了基础。更重要的是,政党应当超越短期选举周期的限制,致力于长期的社区建设和政治教育,增强公民的组织感和归属感,唤醒被忽视群体的政治主体性。这一过程的资源并非难以获得。以2024年美国民主党的竞选支出为例,数十亿美元的广告投放虽产生一定效果,但相比之下,若有部分经费用于全年无休的基层组织建设,将带来更坚实和可持续的政治基础。重建大规模会员制政党不仅是一项组织工程,更是一场政治文化的变革。它要求打破对政党功能固化的认识,强调政党作为政治与社会连接桥梁的本质,注重包容性与多元性,推广基层民主,推动开放参与。
只有如此,政党才能重新成为民主制度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总的来看,大规模会员制政党的复兴并非简单重复历史,而是结合当代社会变迁和技术条件,探索符合新时代需求的政党建设路径。尽管困难重重,但通过理性规划和实践创新,政党依旧能够恢复其作为公民与国家之间强有力中介的角色,促进政治的透明、公正和参与。未来的政治发展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能否实现这一转型,并带动整个民主生态系统的积极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