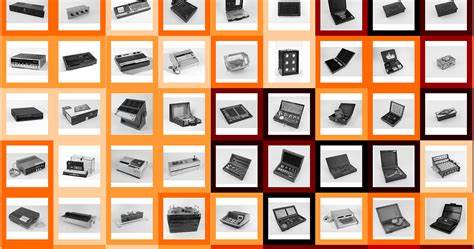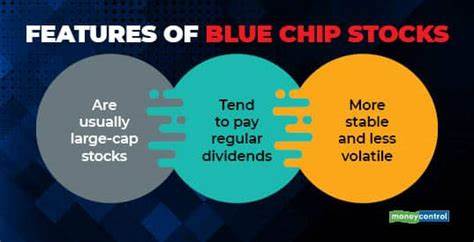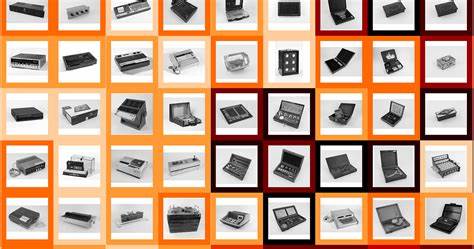科学博物馆作为文化遗产的宝库,拥有丰富的藏品,涵盖从工业技术到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然而,绝大多数博物馆藏品常年藏于库房,鲜少被公众直接观赏。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线展览逐渐成为连接公众与文化遗产的重要桥梁。而计算机视觉技术的引入,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探索博物馆藏品途径。2020年,科学博物馆集团利用计算机视觉分析了其超过7000件藏品,通过颜色与形状的深度挖掘,展现了一个多维度、动态变化的博物馆世界。通过对不同年代的物品进行比较,从颜色的演变到形状的变迁,计算机视觉不仅帮助理解藏品的历史背景,更推动了数字馆藏的创新展示和用户交互体验。
在线藏品的研究赋予我们前所未有的视角。相较于传统的实体展览,数字图像能够让我们跨时空、跨地域地检视藏品的细节。科学博物馆此次选取了21个类别的藏品,这些类别多为大众熟悉的日用物品,如摄影技术、计时工具、照明设备、打印与书写用品、家用电器及导航工具等。分析这些对象的颜色、形状和纹理,揭示了设计美学与材料科技的时代变迁。 颜色作为物品的第一视觉元素,其在藏品中的分布与演变尤其引人关注。研究显示,在这7000多件物品中,最常见的颜色是深炭灰色。
这一颜色在80%以上的藏品中出现,虽然单个图片中比例较低,但它的普遍性反映了工业设计中色彩的守恒性。与此同时,历史时期的对比揭示出一个有趣的趋势:随着时间推移,物品的颜色逐渐变得更加灰暗,棕色和黄色则有所减少。这一变化很可能与材料的变迁有关,尤其是由木制品向塑料制品的演变。六十年代以后,鲜艳饱和的颜色开始渐渐流行,为工业设计注入更多活力与多样化的视觉效果。 深入个别物品的颜色分布,也可见丰富多彩的细节。以1900年生产的Century Model 46板式相机为例,其内部细节呈现出丰富的颜色层次,超越了单一色调的简单印象。
对比1844年克库和威特斯通双针电报机与2008年至2010年间的iPhone 3G手机,不难发现旧时代电报机的色彩多样性,主要源自其采用的红木材质及复杂的造型,而现代手机则以金属和塑料为主,更注重简洁的线条和双色调设计。这里的差异不仅仅体现了材料学的进步,也反映了设计美学的演变。 此外,通过计算机视觉分析,还能够探测出肉眼难以发现的“隐藏颜色”,如19世纪怀表中少量存在的蓝色色素。蓝色多半来自怀表内部螺丝的热处理工艺——蓝色氧化层不仅兼顾了防锈功能,也为藏品增添了独特的视觉特征。此类细节的发现,丰富了我们对历史工艺流程和设计技术的认知。 在颜色丰富性的比较中,某些藏品因其包装或附属物呈现出高色彩多样性。
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香烟广告包及胶卷盒,到80年代的电脑及桌面游戏,这些新兴消费文化的产物以其多样的颜色代表了市场的变迁与文化的活跃。 研究还揭示了电话这一特殊类别的颜色演变。科学博物馆藏有成百上千的电话,从19世纪晚期到现代。早期电话与当下智能手机依旧共享黑银双色调,而20世纪中期的电话色彩则更加多元。随着80年代“砖头机”电话的普及,整体配色趋向单调,这种“去色彩化”体现了工业设计对功能主义的偏好。 除了颜色,形状与纹理同样揭示了技术与审美的变迁。
通过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结合降维与聚类方法,研究人员构建了基于视觉特征的藏品地图,将相似形态的藏品聚集在一起。研究发现,现代物品尤其是二战后,形状趋于方正简洁,“盒子”成为最常见的形状,涵盖香烟盒、电视机、手机、电脑游戏盒等不同类别。这种趋同性说明工业设计中功能与生产工艺对形状的制约。 然而,这一趋势也有例外。比如中间位置聚集的桌面电话,造型复杂且具象征性,展现了设计师对美学的追求以及当时技术限制下产品工艺的特色。东南角的半透明物品群则表现出玻璃与装饰用途的多样形态,声情并茂地诠释了材质的艺术表达。
地图上还有多个“孤岛”——独特的藏品群体。如打字机以其复杂部件和机械结构独树一帜。打字机的滚轴、色带、回车杆等构造不仅功能丰富,也赋予其极具辨识度的形态。这个历史阶段的办公工具,正如一篇1901年纽约论坛社论所言,若一周内禁止使用打字机,商业世界将陷入不可想象的混乱。 除了群体特征,计算机视觉还帮助识别极具个性化的单件藏品。文中展示了几件独特的家庭用品,如糖果切割器、利用余热循环的加热器及手摇刨丝器,还有两件装饰艺术风格的立体相框与扬声器。
特别是诺诺拉观影器,这种如翻页书般的设计,颇具互动性与时间感。甚至人工草坪和蓝色碎玻璃这样与回收再利用相关的创新物品,也在博物馆的数字地图中占有一席之地,彰显可持续发展的精神。 通过计算机视觉研究,科学博物馆的数字藏品展现出一种时代脉络下的设计进步与文化沉淀。颜色渐趋灰暗、形状越来越规整的趋势,反映了工业化与材料科学的双重推动。同时,面对现代观众,如何将这些“黑盒子”变得生动且富于吸引力,仍然是博物馆数字化转型的一大挑战。 该项研究也揭示了数字博物馆领域常见的技术难题。
首先并非所有藏品均已数字化,部分采用黑白照片,或因拍摄环境影响,如背景不均匀导致颜色提取困难。其次,颜色识别依赖于算法对边缘颜色的准确判断,阈值设定需保持平衡,避免包含背景色或遗漏细节。此外,视觉相似度的计算虽然精确,但不考虑物体的实际大小,可能导致尺寸相差悬殊的藏品被误判为相似,增加展示时的复杂度。 环境光线、拍摄角度及设备的不同,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颜色和纹理的表现,使得同一藏品的数字影像表现差异较大。随着博物馆藏品的不断扩大及数字拍摄技术的提升,这些挑战将逐步得到解决。计算机视觉与人工智能技术的持续进步,也让对藏品的深入研究和多样化展示成为可能。
展望未来,借助科技手段,博物馆不仅可以丰富线上展览功能,也有望实现更加个性化的用户体验,如根据颜色、形状甚至纹理进行智能搜索与推荐,增强用户探索的趣味性。计算机视觉的应用还能够揭露藏品细节,辅助修复和保护工作,成为文物研究与管理的重要工具。 总结而言,科学博物馆集团利用计算机视觉对藏品进行颜色与形状的深度分析,不仅推动了数字藏品的可视化与互动设计,也为理解工业设计及材料文化的演变提供了全新视角。随着数字博物馆概念的不断成熟与技术的革新,这样的研究将为公众呈现更加丰富多彩、生动立体的文化遗产体验。未来,计算机视觉将在全球各大博物馆的数字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激发人们对历史、艺术与科技交汇之处无限的好奇与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