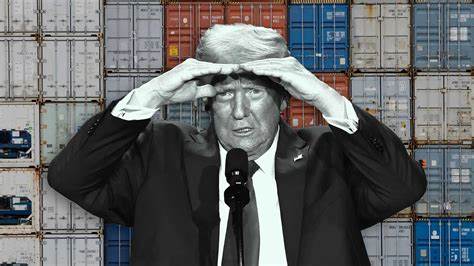近年来,美国对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显著提高,现今的关税水平已达到特朗普执政前的十倍。这一政策变化不仅对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影响,也极大地改变了企业和消费者在供应链中的成本承担结构。投资经理、Aristotle Pacific的董事总经理杰夫·克林格霍弗(Jeff Klingelhofer)指出,虽然以往消费者往往是关税增加的主要承受者,但如今消费者的承受能力已接近极限,企业不得不承担更多这部分成本。 关税的增加本质上是一种贸易壁垒,意图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国外低价商品的冲击。然而,关税成本最终如何分摊,决定了其对经济不同层面的影响。传统上,进出口商和供应链中的各种企业会将关税成本向下游传导,消费者承担最终成本。
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nstitute for Supply Management)曾在调查中确认,大部分供应商确实将关税成本完整转嫁给消费者。2018到2019年间的小规模关税政策研究表明,几乎100%的成本被转嫁给了终端消费者。耶鲁大学预算实验室估计,关税政策平均使美国家庭每年增加近2836美元的额外支出。 但如今的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克林格霍弗强调,美国消费者已处于“资金枯竭”状态,他们面对房价、食品及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已多次上涨,债务负担沉重。根据美联储的数据,当前有77%的消费者还背负着某种形式的债务。
消费能力的下降使得企业不再能够简单将关税成本转嫁给最终消费者。相反,利润率居高不下的企业开始吸纳更多的关税成本,以避免削弱消费者需求。 事实上,企业的盈利能力近年来持续走高。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不断攀升,2021年达到历史最高点13.6%,2025年初仍维持在12.8%左右。强健的企业财务状况为吸收贸易摩擦带来的额外成本提供了空间。在舆论压力和政策层面的影响下,部分大型企业更倾向于承担与关税相关的费用,避免因涨价而导致消费者流失。
特朗普总统此前公开斥责沃尔玛,要求零售商“自行承担关税成本”,这一事件反映出政治因素也成为推动企业吸收关税的一股力量。 当前中美贸易谈判陷入僵局,关税水平保持高位震荡。此种态势使得投资者和市场观察人员更加关注关税对经济的具体冲击程度。克林格霍弗指出,美国的整体经济体系存在高度脆弱性,关税如同一种震荡因素,其影响深浅将取决于谁最终为其买单。消费者的购买力被极度压缩,直接将成本转嫁给他们可能抑制需求,反而使企业面临更大风险。因此,更多企业开始选择通过压缩利润率、优化成本结构等方式来缓冲关税带来的压力。
这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内部效率的提升和业务模式的转变。进口关税的提升激励企业积极寻找替代供应商,或者调整生产线,推动更多环节本土化、近岸化,以减少对高关税进口商品的依赖。同时,许多企业在供应链管理方面加大数字化和自动化投入,寻求在成本控制和流程优化上取得突破。但这些调整通常需要时间,也带来额外投资压力。 对消费者而言,虽然暂时得以避免更大幅度的价格上涨,但关税在企业利润中被吸收远非长久之计。部分企业可能因利润被压缩影响长期投资和创新动力,经济增长潜力或受限。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无法持续承担成本,最终关税负担仍有可能转嫁给消费者,届时消费市场可能经历剧烈波动。 此外,关税的升高对全球供应链结构也带来不确定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受到冲击的背景下,高关税阻碍商品自由流通,增加贸易成本,抑制跨国企业的效率。此外,贸易摩擦加剧还可能激化全球经济竞争,促使各国采取相应的保护主义措施,进一步影响全球市场稳定。 综上所述,美国关税水平激增已成为经济中的重要变量。消费者负债率居高不下,已难以承担更多额外支出,使企业不得不在利润空间中消化新增成本。
虽然企业短期表现出较强的盈利能力,但长期依赖高利润率掩盖关税成本的策略存在风险。有效平衡关税政策、市场需求和企业盈利之间关系,既是政府的难题,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挑战。未来,伴随国际贸易环境的复杂多变,企业将更加注重创新,优化供应链结构,以增强抵御贸易风险的能力。同时,消费者支出状况和投资趋势将继续牵动经济的走向,所有市场参与者需密切关注这一不断演变的局面,为应对持续高关税带来的冲击做出科学合理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