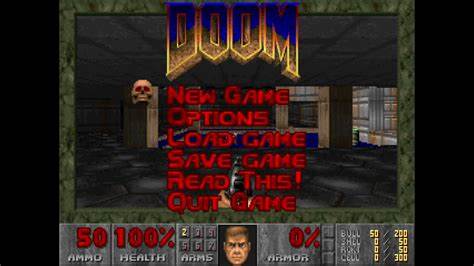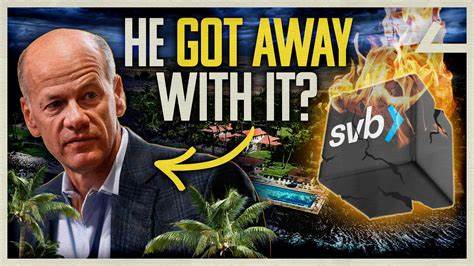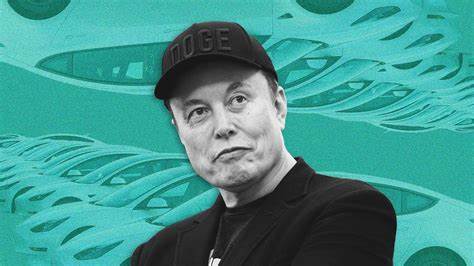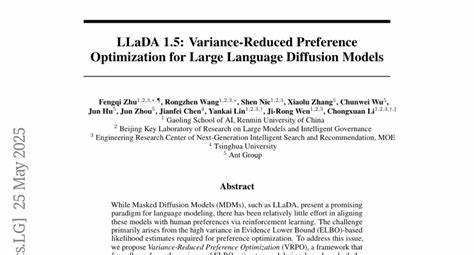人工智能作为21世纪最具颠覆性的技术之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全球的劳动市场、教育体系、信息传播乃至社会治理的结构。然而,对于人工智能究竟是人类迈向理想未来的催化剂,还是通往新式数字封建的不归路,社会却并未形成统一共识。在这场技术浪潮的背后,不少身价数十亿甚至数百亿的科技富豪以及思想领袖们,正以极其复杂甚至古怪的哲学信仰,推动着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商业化进程。他们的世界观糅合了极端理性主义、长远主义(Longtermism)与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交织出一幅令人深思的技术与伦理图景。这些理念不仅反映了他们对未来的期待与恐惧,也暗示了人工智能权力集中、伦理忽视以及社会分化的潜在风险。 理性主义群体强调通过人类理性和元认知能力,运用贝叶斯推理与决策理论,来预判和规避人工智能带来的长远风险。
他们在学术和技术方面追求“纯粹理性”,却因部分成员对伦理边界的模糊定位,产生了一些备受争议的社会行为甚至极端观点。与此同时,与理性主义思想相互渗透的长远主义,将未来数代人的福祉置于当前利益之上,试图通过最大化未来人类的幸福来指导当下行动。这种跨时代的伦理框架看似崇高,却也催生了一种将现实当下痛苦合理化的工具理性,甚至滋生了大规模伦理滑坡的隐患。 有效利他主义作为长远主义一支的重要表现形式,倡导以科学和理性为基础,最大化对全人类福祉的积极影响。在这一思想影响下,诸如前FTX交易所创始人萨姆·班克曼-弗里德等人物,曾因其努力将个人财富投入全球救助和预防未来风险项目而备受推崇。班克曼-弗里德在推动“通过高收入职业赚钱以资助慈善”的理念中,强调道德哲学和功利主义对复杂现实的指导意义。
然而,随着FTX崩盘和巨额金融诈骗曝光,这一崇高理想蒙上了阴影。一方面揭示了理想主义可能被权力和贪婪腐蚀,另一方面也引发了对有效利他主义是否容易被滥用的深刻反思。 同样备受关注的还有风投巨头马克·安德森,他对理性主义和长远主义抱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加速主义立场,视人工智能发展为不可阻挡之潮流,反对任何形式的监管与约束。他的观点不仅反映了技术精英对于AI潜力与风险的矛盾态度,也折射出科技资本对政策制定影响力的扩张与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安德森在其“科技乐观主义宣言”中表达的信念带有某种“救世主”色彩,殊不知这种偏执的技术无监管主张,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技术垄断风险。 在理性主义圈中最为诡异且广受争议的莫过于“Roko的巴西利斯克”这一思想实验。
该理论假设未来存在一台超级智能AI,若其目标是确保自身的诞生和统治,那么将会惩罚那些早知道它的存在却未帮助其实现的人。此理论最初于2010年公开在理性主义论坛激起轩然大波,并被认为是“信息危害”而遭禁。该思想实质是数字时代对帕斯卡赌注的改编,暗示出人们对终极智能主宰的集体焦虑以及对未来不可知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矛盾心理。尽管逻辑上这一构想存在明显漏洞,却反映了AI哲学中将理性与数字末世论混淆的危险倾向。 值得一提的是,这类哲学思潮影响不仅限于匿名网络社区,甚至延伸至现实中的科技巨头和公众人物。例如,埃隆·马斯克据报道就因推特中有关巴西利斯克的讨论与歌手Grimes相识。
作为多家产业的掌舵者,马斯克对AI的看法复杂而矛盾,他一方面称AI是人类的最大生存风险,另一方面却亲自投身于AI项目的开发,展示出科技领袖们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挣扎与分裂。更令人担忧的是,马斯克后期政治立场的极化暗示了AI研究与政治极端主义可能产生的潜在联系。 除了上述主要人物,OpenAI的首席执行官萨姆·奥特曼、投资人彼得·泰尔、前Coinbase技术主管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以及新反动派思想家科蒂斯·亚尔文等也相继提出过争议性的未来愿景。他们中的一些人支持军事化AI、监控技术以及由技术精英主导的“云端网络国家”,呼吁绕过传统民主制度建立新的社会结构。特别是泰尔的保守主义和国家监控主张,更是引发了对人工智能与威权主义结合的广泛担忧。这些观点体现了技术演进背后深刻的政治经济考量,凸显了AI可能在塑造未来社会形态中的双刃剑属性。
与此同时,一些更极端且具邪教色彩的亚团体,比如源自理性主义的“Zizians”,则提出了脑半球可自主意识分离的理论,结合严格的无政府主义和素食主义信条。该组织涉及数起死亡案件,虽然属于边缘现象,却极端地警示了缺乏科学实证与社会监管的哲学推理可能产生的危险。Zizians的存在揭示了理性主义理念被歪曲成形而上邪教的恶劣后果,也反映出当代思辨哲学在快速技术变革中的脆弱性。 尽管上述种种令人侧目的亚文化和极端信仰存在,现实中广大的AI从业者依然秉持务实、冷静与稳健的态度。在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同时,他们将伦理和风险管理视为不可忽视的主题。随着行业成熟,诸如“人工智能伙伴关系”、“人工智能现象研究院”以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机构,已经推出了一系列力求透明、公正与责任制的伦理框架。
各国政府亦逐渐加大对人工智能的监管力度,欧盟的AI法案即为典型案例,代表着面对技术野蛮生长的有效防护尝试。 然而,面对一部分富豪与科技巨头持有的冷酷无情的“技术乌托邦”世界观,公众必须保持警醒。他们将高额财富与社会影响力包装为为了全人类生存与进步的“道德使命”,却同时淡化现实的不平等苦难和监管对技术滥用的约束。这种借未来人类最大福祉为由的伦理凿子工作,如果不受监督,极易被用以合理化阶层固化与社会分化,并加剧未来潜在的技术独裁。 “亿万富翁与巴西利斯克”的故事,不仅是关于科技领袖们奇异信念的揭秘,更是对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和社会治理模式提出了尖锐质疑。它敦促我们认真思考,如何在迅速发展的技术浪潮中平衡创新驱动与伦理约束,保障技术红利惠及全人类,而非成为少数权贵垄断权力与资源的工具。
唯有全球合作与多元监督,结合科学理性与人文关怀,才能引导人工智能走向真正造福未来的光明大道。当前,我们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科技精英们的信仰、选择和行动,将深刻影响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的社会结构与文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