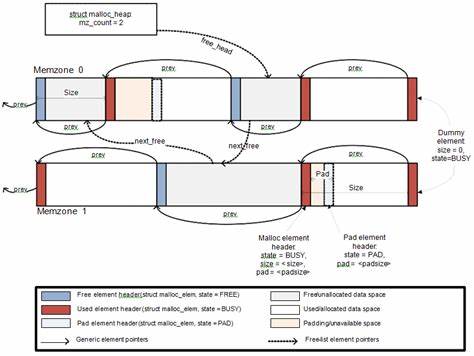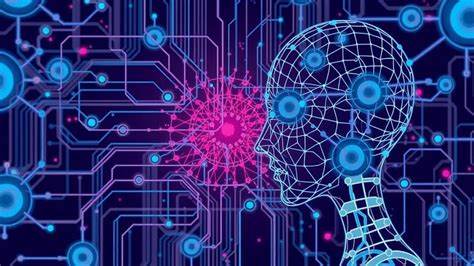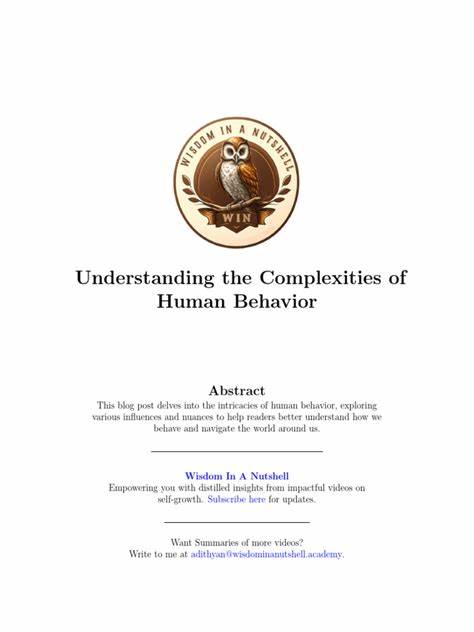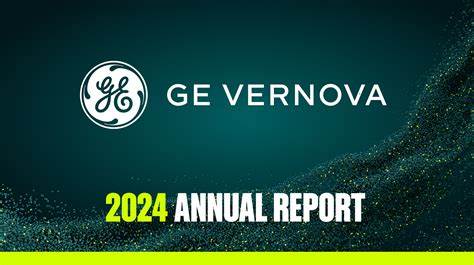近年来,全球塑料污染问题日益严峻,成为环境保护领域最为紧迫的议题之一。每年约450万吨新塑料被生产,预计到2060年这一数字将因生产增长而翻三倍,不仅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还带来严重的人类健康风险。塑料废弃物的广泛分布,从最高峰的珠穆朗玛峰到地球最深处的海沟,无处不在地污染土壤、水源和空气,甚至渗透到人体组织中。如何有效管控塑料生产和使用,成为国际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主持的全球塑料污染条约谈判,旨在制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协议,以减少塑料污染的危害。然而,自谈判开始以来,塑料工业联手产油国家对限制塑料生产的提议进行了强烈反对,导致谈判进展受阻。
这些利益相关方利用丰富的资源和影响力对谈判过程深度渗透,影响协议内容,延缓关键决策。业内大量公司和国家代理人组成的游说团体频繁出现在会议现场,其人数远超参与谈判的国家代表和独立科学家。例如,在近一次于韩国釜山举行的谈判中,来自塑料行业的游说者多达220人,超过东道国代表团成员数量的数倍。这些利益集团通过直接介入谈判甚至控制关键委员会成员,为其利益发声,弱化科学证据的重要性,不断主张以回收和废物管理代替对塑料生产的限制,强调技术创新和循环利用可以解决问题。这背后,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尤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因其经济高度依赖石化产业,在条约谈判中握有关键话语权。沙特通过其国有企业沙特阿美及旗下的塑料生产公司Sabic,积极影响谈判方向,不断反对塑料生产上限的设立。
同时,沙特与UNEP有着密切合作关系,提供了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使得UNEP官员在谈判态度上受到质疑。UNEP执行主任因格·安德森曾发表言论,试图淡化塑料生产总量限制的必要性,强调应区别对待一次性塑料和长寿命塑料制品,这一立场引发环保组织的广泛批评,认为这无视了塑料生产本身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环境组织和科学家忧虑,这种软化立场可能导致条约目标被大幅削弱,谈判范围狭窄化,难以实现根本性的污染减排。与此同时,科学界试图填补官方科学咨询缺失,成立了独立的科学家联盟,致力于提供证据支持和观点指导,但复杂的谈判环境和信息封闭使其作用有限。权威专家反复遭受来自工业利益代表的骚扰和威胁,甚至在正式联合国会议上出现骚扰事件,部分科学家不得不采取诸如隐私保护措施以防止监控和信息泄露。塑料产业游说团体以“社会观察员”身份参与谈判,却因资金和资源优势,具有极大影响力,他们经常出现在国家代表只能有限进入的讨论环节。
这种不对等的参与度令那些代表受污染社区、环保组织及科学研究人员的声音被边缘化,削弱了谈判的公平性和有效性。资金成本高昂也加剧了这种失衡——相较于资源充裕的工业集团,中低收入国家及独立团体难以承担长时间国际谈判的旅费和住宿,削弱了他们在谈判桌上的代表力量。塑料生产的迅速增长,已成为气候变化的重要推手之一,主要源于塑料绝大多数依赖石油和天然气为原料,相关产业的碳排放不容忽视。因此,若没有对塑料生产施加明确的限制,全球气候目标将难以实现。多位环境法律专家指出,目前塑料行业所提倡的回收技术和废物管理方案存在“魔术思维”成分,现实中只有不到10%的塑料实现有效回收,这远远不足以解决污染问题。对于塑料条约的成功,环境保护者强调需要实现“生产上限”,以实际减少塑料的生产量,切断塑料污染的根源。
然而,石油输出大国和塑料生产企业希望通过谈判将焦点转移至废弃物处理,继续扩大生产规模。国际社会对此展开激烈争论,并对谈判进展表达担忧。尽管如此,超过100个国家联合1000多名科学家联署呼吁实施生产上限,以确保对环境和健康的切实保护。法国环境部长在2025年联合国海洋会议上发出严厉警告,指出塑料大量堆积已“窒息生态系统,毒害食物链,威胁我们子孙的未来”,强调当前时刻至关重要,不能放弃斗争。全球塑料污染条约的未来形势复杂多变,谈判进程充满不确定性。塑料工业的全面渗透不仅体现在谈判场上,也反映了全球治理机制在平衡多元利益时的挑战。
解决塑料污染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科学证据应成为决策的核心,利益冲突需被有效管控,国际合作必须排除妨碍可持续发展的力量。唯有加强透明度、限制利益集团对谈判的过度介入,并强化对生产总量的约束,全球塑料污染问题才能迎来曙光,从而保障地球环境的可持续未来和人类的健康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