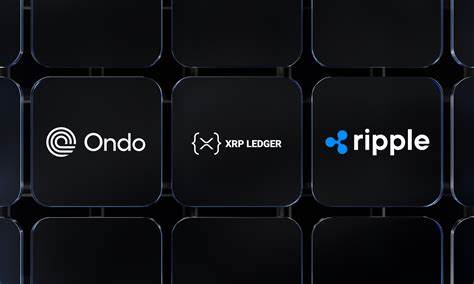在印度这样一个多语言、多文化交织的国家,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尤其是英语,作为殖民历史遗留下的语言遗产,其地位既被视为通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关键,也承载着沉重的历史包袱和复杂的文化矛盾。对于许多印度人来说,掌握英语意味着接触更广阔的世界和更多的机遇,却也意味着面对语言歧视和文化身份的挣扎。作为一名翻译者和双语诗人,作者Hemang Ashwinkumar的经历深刻反映了这种语言文化的多重矛盾和心理挣扎。作者自幼接受母语古吉拉特语的教育,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的迟来介入,使其在语言学习中经历了诸多困难与羞愧,也在不同语言社区中感受到身份认同的撕裂。学术追求过程中遭遇的语言歧视和排斥,充分体现了印度社会存在着语言优劣等级的现实问题,英语与地方语言的对立以及由此带来的人际隔阂与社会偏见。
作者的经历并非个例,而是许多印度学生和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印度的语言政策往往凸显了这一问题。尽管母语教育被广泛倡导,实际执行中英语的普及度和其在教育、就业中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社会阶层和文化资本的象征。英语教育资源的集中和不均衡分配,也进一步加剧了城乡、阶层之间的语言鸿沟。许多以母语为主的学生由于缺乏有效的英语语言能力,常常感到被边缘化,甚至产生语言歧视的心理压力。这种羞愧不仅是对个人语言能力的质疑,更是对自身文化身份的质疑和社会归属感的挑战。
与作者的个人故事相呼应,印度文学界的语言现象也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像Ngũgĩ wa Thiong'o这样伟大的非洲作家,选择放弃用殖民语言英语写作,转而采用自己的母语进行文学创作,以反抗殖民遗产,彰显文化自信和语言自主权。然而,他并未完全放弃英语,而是试图通过翻译将母语作品带入英语语境,打破语言间的壁垒,实现跨文化的对话。这一策略彰显了语言的双重角色:既是文化认同的载体,也是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正如作者所感悟的,真正的语言力量在于其能够促进人类的理解和尊重,而非制造分裂与羞辱。在印度,英语的地位尤为复杂。
它既是全球化的通行证,又被一些人视为文化入侵的象征。政府和社会面对这一矛盾时,往往倾向采取“一刀切”的语言政策,如强化母语教育或限制英语使用,但这种策略忽略了语言的多样性和互动性。正如作者提出的观点,转嫁羞耻感于英语而非地方语言的做法是错误且无益的。真正的挑战在于打破语言的阶层划分,消除以语言为标准的歧视和偏见。教育体系中的语言政策也需要改革,以包容多语言学习环境,同时赋予地方语言以应有的文化价值和现代功能。翻译的角色在这一进程中尤为关键。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技术,更是一种文化的桥梁和身份的调和机制。印度作为一个存在多语种共存的国家,翻译实践既是一种文化传递,也是一种促进社会融合的手段。译者通过挖掘各种语言中的文化内涵,打破语言间的隔阂,有助于推动不同社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印度人“生活在翻译中”的现实,恰恰揭示了多语言环境下语言交织的复杂性,以及跨语言交流对文化认同与社会和谐的重要意义。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英语无疑是联系世界的重要语言。作者认为,尽管英语有其殖民的历史负担,但合理使用和接受,可以成为理解多元视角和促进文化交流的工具。
英语为全球视野提供了“千眼”的可能性,有助于人们摆脱狭隘的文化视野和偏见。印度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如甘地和泰戈尔,都没有将英语视为羞耻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传播思想、交流文化的重要媒介。他们的实践印证了:语言本身无所谓正误和高低,关键是使用者的态度和精神。语言可以成为自我表达和社会沟通的桥梁,也可以演变为歧视和压迫的武器。要消除语言带来的羞耻感,必须超越语言本身,关注其背后的社会结构、文化权力与认同政治。作者深感羞愧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语言被用来剥夺人类的尊严和权利。
每当学生因压力而自杀,达利特和部落女性遭受歧视时,语言的阶级和文化功能便暴露出其阴暗面。而真正值得追寻的,是那种超越言语的“无羞耻语言”,它不制造分裂而是促进平等,恢复人性和尊严。这是一种跨越语言界限的真理,是对人类共同命运和精神自由的深刻认知。总的来说,印度人面对的“语言羞愧”不仅反映了个体的心理困境,更映射出社会结构中的深层矛盾。英语在印度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我们必须拥抱语言的多样性,消除基于语言的歧视和偏见,推动翻译和跨语言交流,实现真正的文化共荣。
只有如此,语言才能成为连接人心的桥梁,而非隔阂的高墙。作者的经历和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证明了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文化认同和社会正义的载体。未来的印度,期待在多语共融的基础上,汇聚多元文化的智慧,实现人人平等的语言环境,真正破除“英语羞愧”,走向更加包容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