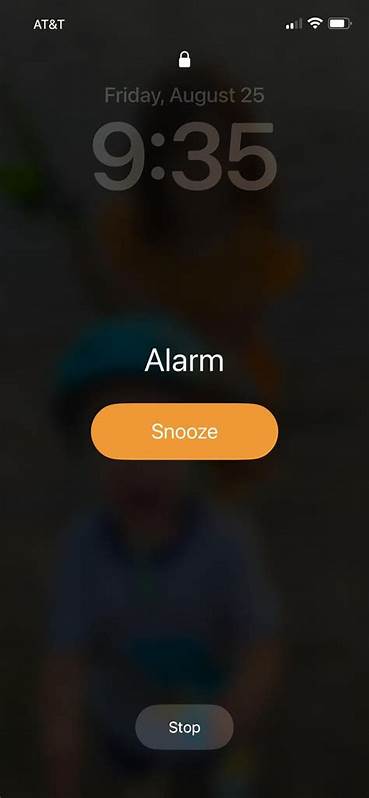班尼頓(Benetton)這個品牌自1965年成立以來,一直以其鮮明的風格與獨特的市場定位被世人所熟知。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班尼頓以其大膽且充滿衝擊力的廣告,將品牌激進主義推向了巔峰,廣告內容聚焦於多元文化、種族融合以及社會議題,勇於挑戰當時的社會禁忌。然而,這種風格在帶來話題同時,也讓品牌背負了長期的爭議與批評。隨著市場和消費者價值觀的演變,班尼頓的品牌形象也陷入了混亂與矛盾,成為研究品牌如何平衡社會責任與商業成功的重要案例。班尼頓早期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來自於與著名攝影師奧利維耶·托斯卡尼(Oliviero Toscani)合作推出的“聯合色彩”(United Colors of Benetton)廣告系列。這些廣告主題涉及種族平權、性別多元、愛滋病議題等,甚至公開呈現如愛滋病毒患者的臨終鏡頭、新生嬰兒的臍帶照片等充滿挑戰性的影像。
這種極具挑釁性的表現手法,在當時掀起軒然大波,受到大眾和監管機構的強烈關注與爭議。即使面對投訴和反對,班尼頓堅持通過廣告呼籲社會正視被忽視的問題,試圖將企業的商業宣傳與社會變革結合起來。此後,班尼頓並沒有止步於此,而是不斷將品牌激進主義往更深層次推進。例如2011年的“UNHATE”基金會活動利用政治領袖間親吻的合成照片,試圖傳達反對仇恨文化的信息。儘管該活動在2012年戛納廣告節獲得了嘉獎,但因涉及宗教領袖而引起梵蒂岡的抗議,部分廣告被迫撤下。這些爭議性的行為再次證明班尼頓永遠不按常理出牌,願意為社會議題冒險,但也引來更多聲浪質疑品牌是否真正關心社會抑或只是為了引起注意。
除了廣告領域的激進主義,班尼頓在實際企業行動中亦遭遇巨大挑戰。90年代,班尼頓成為阿根廷最大私有土地所有者,卻因土地使用爭議與當地原住民馬普切(Mapuche)發生衝突。多次抗議與佔領活動中,甚至出現了包括活動家聖地亞哥·馬爾多納多(Santiago Maldonado)失蹤身亡的悲劇,引發國際關注。此外,班尼頓曾因涉嫌使用侵犯消費者隱私權的RFID追蹤晶片而遭遇消費者抵制,並面臨動物權益團體PETA針對其羊毛採購行為的抵制,這些事件進一步衝擊了其作為負責任品牌的形象。更嚴重的是2013年黎明廣場(Rana Plaza)建築物倒塌事故,該廠內生產班尼頓商品。遇難人數超過1100人,此事件成為全球最嚴重的服裝業安全事故之一。
起初,班尼頓否認與該工廠有直接關聯,後來證據證實其商品來自這家工廠。儘管隨後班尼頓承諾進行賠償,但最初未積極參加補償協議和賠付,招致全球消費者與社會運動者的強烈抗議。這不僅損害了品牌信譽,也反映出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際執行存在巨大落差。在與當代其他品牌如耐克(Nike)比較時,班尼頓的品牌激進主義顯得較為混亂和未能形成明確持久的品牌價值。耐克在推出涉及社會正義運動的廣告時,雖然同樣充滿爭議,但憑藉明確的立場和精良的市場運作,成功獲得商業上的巨大成效,包括品牌價值和銷售的顯著提升。相反,班尼頓似乎未能與時俱進,反而因為產品設計過時、價格競爭力下降以及全球零售管控薄弱,導致品牌影響力日益式微。
許多評論者指出,班尼頓的廣告效果已不如以往,甚至令消費者產生負面情緒,並削弱了品牌在服飾市場的競爭優勢。班尼頓的市場地位也反映出其品牌激進主義帶來的雙刃劍效應。當品牌觸及社會敏感話題,如死刑犯肖像、難民照片等,雖然意圖引發社會關注,但消費者質疑其是否將人性尊嚴與服飾銷售混為一談。這種將悲劇與商業宣傳結合的手法,對部分潛在客戶而言具有反感效果。再加上品牌在不同國家市場採用分裂的行銷策略,如印度分公司推出名為#UnitedByCause的以「善良」為主題的數位宣傳,與其他市場的強烈爭議風格形成反差,顯示品牌管理缺乏統一方向與凝聚力。這種矛盾局面也讓業界及消費者重新審視品牌激進主義的真正意義。
品牌運動雖能快速引起關注並提升品牌話題度,但過度依賴爭議手段,容易讓真正的社會議題淪為商品銷售的工具,淡化其社會影響力。同時,品牌本身若無法在產品質量、客戶體驗和市場策略上保持競爭力,再多的社會訴求也無法長久支撐其市場地位。如今,班尼頓處於一個轉型期,迫切需要重新評估其核心品牌價值,並決定未來如何在社會參與與商業目標間取得平衡。重拾早期強調全球和諧與多元包容的品牌精神,或許能幫助其重建消費者信任與市場影響力。然而,只有將激進主義與企業責任真正融合,並建立透明誠信的對話,班尼頓才能走出品牌困境,將爭議化為長遠發展的契機。綜觀班尼頓的品牌故事,不僅是一段商業歷程,更是一場關於品牌道德與社會責任的深刻實驗。
它提醒企業,品牌激進主義並非只是一條引起爭論的捷徑,而是需要承擔相應風險與責任的長期承諾。這種理念的缺失,或許正是班尼頓多年來在激進主義道路上跋涉卻未能實現商業和社會雙贏的關鍵所在。未來,班尼頓能否在激進中找到真誠與穩固的立足點,值得業界和消費者持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