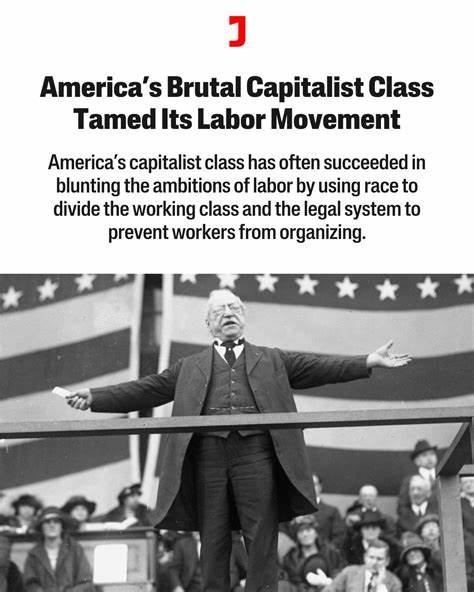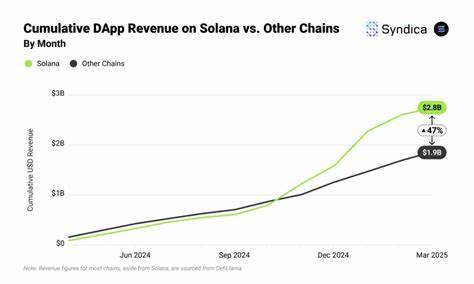在全球范围内,工会不仅是劳工权益的代表,更是推动社会福利、普及医疗保障和保障工人福利的重要力量。欧洲的工会纷纷以政治诉求为重心,推动普遍的社会福利体系,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导力量。然而,美国的工会发展路径则展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美国资本阶级的残酷本性和历史上的种种阻碍,使美国劳工运动长期局限于作为私人保险的提供者,难以成为具有广泛社会变革力量的政治团体。美国劳工运动为何如此“不同”?这一问题的答案,需回溯到20世纪初乃至更早的社会政治环境。相比于法国工会的革命工团主义和德国工党及其工会联盟主张的全民福利,美国工会在1894年放弃成立独立劳动党的行动标志着其政治战略的转折。
美国劳工联合会选择了以“面向自身成员的分权式谈判”为优先目标,常常忽视其他社会工人的整体利益。此举直接导致了美国工会在支持国家层面福利制度上的消极态度,并且积极反对当时多个促进公共福利制度的提案。历史学者们如迈克·戴维斯等人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这种孤立局面,并非偶然,而是特定社会经济条件和政治压制交织的结果。种族、民族、宗教和地位的分裂极大削弱了工人的团结力量。早在20世纪初,社会学家W. E. B.杜波依斯便指出,美国有色人种工人在工会中的比例极低,且工人内部存在北方白人与南方有色人种工人对立的状况。资本家和政治精英通过促进种族对立和利用特别的历史脉络,成功制造了工人阶级的分裂局面。
与欧洲工人阶级整体向社会主义和团结方向发展的趋势不同,资本主义美国的工人阶级在利益定位上往往陷入“劳工贵族”现象。许多白人工人,尤其是受过一定技能训练的男性工人,由于相对较高的工资和社会地位,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劳动阶层,反对更激进的、以全体工人利益为核心的改革。这种阶级层次的分裂,被著名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称为“劳工贵族”,这种精英化群体往往选择与资本妥协,而非推动彻底的社会变革。美国独特的劳工市场结构和大量移民激增,也加剧了工会内部的语言、文化、宗教和民族差异,使得实现工人阶级广泛团结极为困难。社会学家伊拉·卡茨内尔森指出,美国工人“工作时是工人,家中则是族裔”,这种双重身份限制了他们的阶级意识和政治组织能力。除了社会结构性因素外,美国工人运动还面临着极其严厉而复杂的镇压和法律限制。
早在19世纪中叶,工人集会和罢工几乎处于非法状态。政府和资方常用武装镇压罢工,联邦民兵甚至开枪射击示威工人,这种极端的暴力镇压在美国劳工历史中屡见不鲜。更隐秘但影响深远的则是美国司法体系对工会权利的限制。尽管伴随着《霍特判例案》的判决,工人联合体因提供事故和死亡保险等福利而获得有限法律认可,但大规模的罢工、集体谈判等权利始终难以法定保障。工会之所以依赖福利保险的提供,正是因为它们借此获得了合法身份与生存空间。然而,这也让工会处于一个弱势和被动的角色,只能在局部、分裂的劳工群体之间维系利益,而不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包容各阶层利益的统一政治力量。
美国劳工联合会(AFL)在20世纪初对保险福利的执着,不仅是策略上的选择,更是被逼不得已的妥协。随着《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等一系列法律的实施,罢工和集体谈判的权利被大幅限制,工会被迫把重心放在私有福利的管理上,而非大规模的阶级斗争。1947年颁布的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再次重创工会,极大限制了其罢工和示威能力。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瓦格纳法案》的出台和CIO联合会的蓬勃发展,带来了一段短暂的辉煌时期。在这段时期里,工会不仅组织了许多大型产业工人,也推动了黑人劳工和少数民族的权益改善,为后来的民权运动奠定基础。但这段时期很快被后来的法律回撤和资本阶级重新掌控所取代。
工会的角色又渐渐回归到为会员争取局部福利的轨道。美国工会的资金管理逐渐由资产管理公司掌控,工会内部也因此与资本利益产生复杂的纠葛,进一步削弱了工会作为社会变革力量的独立性和激进性。尽管如此,美国历史上从未缺乏富有政治视野和社会理想的工会组织。早期的劳工团体如劳工骑士团、工业工人世界组织和睡眠车侍从兄弟会等,一直在努力挑战传统的分裂模式,倡导包容性和整体阶级利益的理念。近年以来,像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UAW)主席肖恩·费恩等劳动领导者,也在积极将工会话语扩展到反战、反移民驱逐及反福利削减等社会议题中,试图重塑工会的政治能力。面对美国金融化日益加剧的经济形势,推动工人阶级广泛团结和政治动员依旧充满挑战。
然而,正如历史和现实所示,工会若想真正成为劳工阶级的政治代理,必须超越既得利益集团和狭隘的福利保障,走向基于广泛阶级联盟的变革道路。美国资本主义的残酷和复杂的法律环境曾将工人运动限制在狭小的保险福利范围,但这并非不可逾越的命运。美国劳工运动的未来,依然取决于那些愿意拥抱包容性、挑战现有体制、争取全体工人利益的政治领导者和广大基层工人的共同努力。唯有如此,工会才可能真正“驯服”资本的力量,成为推动社会公正和经济民主的重要推动者,为全体劳动者争取更广泛的权益和福利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