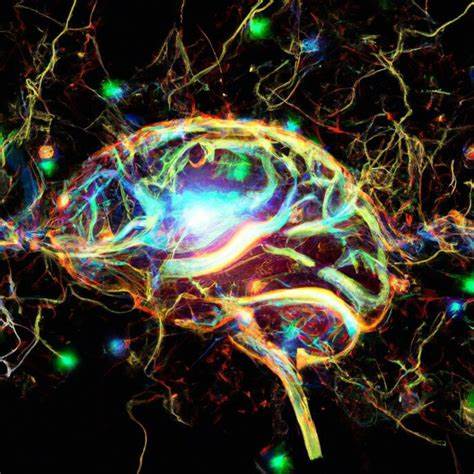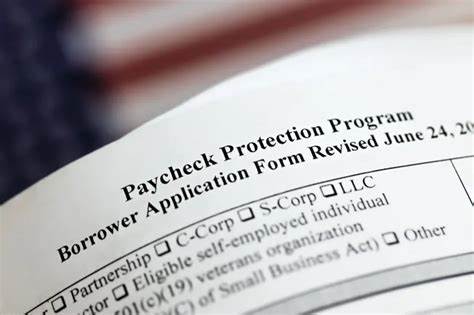意识,这一深刻而神秘的存在,一直是科学、哲学和文化讨论中的热点话题。尽管现代科学在宇宙演化、生物机制和神经科学领域取得诸多突破,但意识本身为何无法被彻底解密,依然令众多学者困惑。探究其根本原因,必须先打破传统科学中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限制,重新审视“经验”这一被忽略的关键因素。四百余年来,科学主要沿着物理主义路线发展,意在以物质、电磁场和大脑神经活动解释意识。然而,意识的主观体验——即我们所称的“存在感”以及对世界的直接感知——始终难以用这些第三人称的客观量化指标说明清楚。哲学家大卫·查尔默斯提出的“意识的难题”正是指向这种解释缺口。
意识的体验并非一般物理过程的简单叠加或衍生现象,而是一种不容易被“硬科学”都能完全涵盖的独特实在。科学在分析意识时,长期陷入了“经验盲点”,这是一种类似于人眼视野中盲区的看不见却又不可避免的缺陷。经验不仅是意识的核心,更是人们与世界交互的基础,是一切认知、情感和思维的源泉。然而,科学从17世纪开始构建的方法论正是意在排除个人主观性,追求可重复、客观测量的“无我视角”,希望从不参杂个人感受的立场研究自然规律。这一视角虽然促进了物理学和实验科学的发展,但却将体验这一不可分割的主观实在边缘化,导致对意识内在性质的忽视。科学史上的热力学发展即是经验盲点的典型案例。
人们首次通过温度计具象化冷热体验,并进一步抽象至热力学理论和统计力学,将体验的“热感”转化为原子运动的数学描述。结果,抽象的物理量被错误地视为比体验本身更真实的实体,虽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却制造了一种哲学上的“替换错觉”,即将模型替代了现实体验。意识问题的复杂性远超该替换框架所能容纳。为克服此困境,科学界和哲学界逐渐回望另一类非传统理解路径,如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和埃德蒙·胡塞尔的现象学。怀特海强调,不应将数学和物理模型的抽象视为比活生生的体验更真实,体验本身是构成自然不可分割的根本。胡塞尔及其追随者主张将意识的主观视角作为研究起点,关注“生活世界”的整体性,拒绝用物质还原论的冷漠目光拆解体验。
与西方主流物理主义的二元对立——物质至上与心灵本体论——不同,这些思潮将经历视为根本,强调整体性和现象的原初性。此外,东亚哲学传统,尤其是印度的中观派哲学,也深入探讨了超越第三者视角的经验本体论,为现代认知科学与物理学的融合提供新思路。拒绝将有机生命简化为机器的物理部件,是新经验科学的另一关键转变。传统科学通常将生物体视为复杂的机械组织,试图通过解析神经元、细胞和分子机制理解意识。然而,生物组织的特点是自我组织性与整体统一性,这种“自创自维”(autopoiesis)性质是机器所不具备的。细胞膜的能动性与循环维持过程表明,生命系统处于不断的开放不是孤立机械,其本质是组织的整体性而非单纯物质堆积。
意识研究的新兴范式,如“行动认知理论”(enactive approach),即从身体、环境和感知的交互中重新定义认知本质。意识不再是被动的接受世界信息,而是主动参与构建自我经验和环境的动态过程。认知与意识牢牢植根于身体感知能力和社会互动,其本质是一种有机的、“在世”的存在活动,这种视角跳脱出传统以大脑为中心的思维机器模型。当前人工智能热潮往往忽视了体现意识关键特征的身体性与生命周期,误将智能等同于计算运算。忽略经验的主体性不仅削弱了对意识的理解,也有可能导致技术伦理风险,因其构建的系统缺乏人性层面中的情感、关爱和社会联系。科学若想真正理解意识,必须改变对现实和认识论的基本观念。
当今量子力学的发展,正暗示了观察者和测量这一经验主体对物理现实不可或缺的地位,反躬自省地呼应着经验优先的哲学立场。人不只是被动观察的外部者,而是互动构成世界的一部分。意识与体验的生物社会环境、感知行为、身体结构紧密结合,是自然不可割裂的组成。人类应把物理学嵌入经验中,而非期待抽象物理概念能完全解释体验。新兴研究不仅探讨生物系统如何编码和处理信息,更强调信息的语义性和自组织性,将生命信息学与经验本体论相结合。此路探索关系认知、意识以至包括未来人造智能在内的智慧形式出现的本质区别和相似性,远比单纯的符号处理模型更具前景。
意识仍旧是现有科学体系中的“盲点”,因为它根植于科学试图回避的主观经验层面。只有正视经验不可还原的整体性、身体性与社会性,将生命视为自我维护的整体系统,科学才能逐渐逼近意识的核心真相。这不仅关乎纯粹的科学认知,更直接关系到科技伦理、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以及我们对自身存在意义的深刻反思。重新把经验放回科学核心位置,以全新生命经验视角重构科学,也许是未来几十年人类文明迈向觉醒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