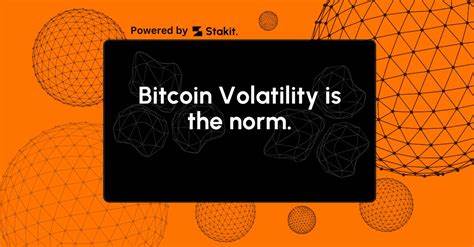区块链技术自诞生以来,依托多种组织结构支持其生态发展,尤其是各大区块链项目背后的非盈利性质基金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基金会在早期为项目提供法律和发展上的缓冲,帮助项目避开诸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监管机构的严密审查。然而,随着市场环境的演变和监管趋于明朗,风投巨头a16z(Andreessen Horowitz)旗下加密部门的头号政策负责人及总法律顾问迈尔斯·詹宁斯(Miles Jennings)公开表示,这种基金会模式已不再适应当前行业发展需求,甚至成为阻碍创新的羁绊。詹宁斯在其2024年6月2日发布的博客文章《加密基金会时代的终结》中详述了原因,并提出了行业升级的路径建议。相较于基金会, Jennings认为通过普通的开发者公司能够更有效地推动网络建设和规模扩张。基金会的初衷是为多个独立参与者提供协调机制,从法理角度突破监管难题,维持网络的去中心化形象。
但实践中,基金会普遍面临协调困难、专业配备不足和效率低下等问题。通常开发团队和业务发展团队被分割开来,缺乏高效协作机制,导致创新和响应速度受限。同时,基金会缺乏市场竞争约束,因为其作为非盈利组织在资金动用上结构性受限,难以像企业一样灵活投放资源以追求成长。更为明显的是,基金会往往成为网络治理中的“影子中心”,少数领域内固化的核心利益集团掌控决策权,实际上削弱了原本意图的去中心化效应。詹宁斯指出,这种结构带来的弊端还包括责任不清晰和法律上的过度保护,因为基金会可以长时间亏损运营,不用面对商业风险,这与需要响应投资者和用户需求的公司形成鲜明对比。以太坊基金会和其关联的盈利企业ConsenSys的关系即为例证。
以太坊网络的发展离不开ConsenSys在中间件、合规服务和开发工具方面的贡献,这种商业实体的参与显著提升了网络的整体生态。而基金会模式在这种功能上表现尤为乏力。业内其他知名项目的领袖也对基金会存在的“去中心化表演”(Decentralization Theater)提出批评。例如,Pinata的联合创始人、CEO凯尔·图特(Kyle Tut)明确表示基金会只是加密世界去中心化“戏剧性”问题的一部分,呼吁摒弃基金会,真正聚焦于构建开放透明的代币体系来驱动技术落地。生态资产管理公司Maple Finance的增长主管Martin de Rijke同样认为,基金会在当前市场更多“拖后腿”,企业化运作能够为市场带来更明确的问责机制和更高的执行力。在监管趋严和政策逐渐明确的环境下,创始人们通过成立基金会的方式选择忽略或隐藏自身对项目的持续影响,这不仅使得法律和实际运作关系复杂,也让基金会成为规避监管的工具,然而这种策略带来了管理效率和激励一致性的缺陷。
詹宁斯总结了基金会存在的四大主要问题,分别为责任缺失、法律经济限制、运营低效以及成为中央化门槛。基金会常规设定为无限期运行且不以盈利为目的,缺乏对市场压力的反馈,也难以拓展商业活动,例如中间件、合规与创新产品等需要公司有更灵活的资源配置。投入研发的团队被各种法律限制分隔开来,导致技术人员与市场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有效协作,阻碍了产品快速迭代和市场适应力。尤其令人担忧的是,基金会背后的实控人和聘用的董事掌舵企业,令代币持有者无法真正参与核心决策,造成了形式上的所有权和实质上的管理权错位。例如以太坊基金会在经历重大升级及领导层调整前,社区情绪低迷,指向其管理方式不被认可。迈尔斯·詹宁斯提出的替代路径是,让普通开发者公司从项目构想到现实产品全面负责。
他们能够高效调配资本,吸引技术和商业人才,并通过明晰的市场反馈机制调整战略,以此实现网络的长远发展。为了确保企业与网络和用户的利益对齐,业界已有多种激励工具可供使用,包括公益型公司架构、收益共享协议、基于业绩的代币归属模式及更多合约保护措施。另有两种日益兴起的组织形式为去中心化非营利协会(DUNA)及“网络治理工具”(BORG),它们可以为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提供合法身份,从而更好地管理治理和资金分配,逐步替代基金会在治理中的传统角色。整体来看,基金会曾为加密行业的原始发展阶段提供了必要的法律庇护和架构支持,其贡献不容抹杀。但随着法律环境的放松和监管策略的优化,加密行业站在了转型关键点,在透明化、市场化及责任明确化方面迈出重要步伐。加密项目如果想与传统金融行业正面竞争,吸引机构资本,将不得不拥抱以公司为主体的治理和运营模式,以更快的决策速度和更强的市场适应性赢得未来竞争优势。
总之,a16z政策负责人迈尔斯·詹宁斯的观点反映了加密行业治理结构的新时代呼声,从基金会到公司化治理的转变,实际上是行业从初创期走向成熟期的必由之路。行业内各方如何在去中心化理念与高效运营之间找到平衡,将深刻影响未来区块链技术及生态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