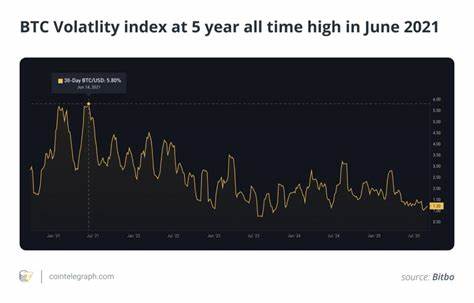在当代劳动结构转型中,一种重要但常被忽视的劳动形态正面临系统性降格:连接性劳动。所谓连接性劳动,是指那些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互动,完成"看见他人、回应他人并建立社会关系"的工作。医疗、教育、护理、社工、心理咨询等传统照护职业显然在其列;但咖啡师、理发师、银行柜员、客服与零售销售等看似"日常"的岗位同样承担着重要的社会连接功能。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欲、技术工具的介入与公共资源的稀缺,共同推动了对这些工作的人为简化与去技能化,进而威胁到公共生活的质量与社会信任的基础。 理解连接性劳动的价值,需先超越对"服务"或"情感劳动"的模糊认知,认识到它同时具备私人与公共双重属性。个体层面,连接性劳动帮助人们在困境时获得被理解与被支持,从而降低孤独感、提升心理韧性并增强对社会制度的信任。
公共层面,这类劳动通过日常交往和制度性互动,织就城市与社区的社会网络,形成某种意义上的"社会基础设施"。没有稳定而有质量的连接性劳动,社会的凝聚力、公共卫生应对能力以及教育公平都会受到长期侵蚀。 资本为何要降格这些劳动?历史与当代的动力是连贯的。早在工业化早期,管理学变革就以提高效率为名,争夺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主张将工人的隐性技能拆解、量化并转移到管理层或机器上,从而实现对劳动过程的集中指挥。哈里·布拉弗曼在《劳动与垄断资本》中对此作出深刻批判,指出资本通过去技能化、标准化和分工的方式,将劳动者变为可替换的"劳动力因素",并以此扩大对劳动过程的支配。
今天,这一逻辑借助数字技术、平台规则与人工智能再次焕发生命力。管理者和平台企业倾向于用数据化指标、脚本化对话、时间表和评分系统来衡量并控制连接性劳动。教育机构把教师拆分为"内容传授者"和"情感激励者";医疗机构引入基于算法的远程诊断与自助问答,将高质量面对面咨询限制为少数付费服务;平台心理健康应用让未受充分培训的"教练"替代专业治疗师,以便降低成本并扩大用户覆盖面。这些变化在表面上提高了可量化指标,但在深层却消解了劳动者自主判断、情境感知与临机应变的能力。 去技能化并非总是立即表现为薪酬下降或岗位消失。资本更偏好的方式是"知识抽取"和"技能再配置":把判断权、知识产权与流程设计转移到管理端或算法中,而把执行端的工作压缩成可监控的动作。
这会造成两种并行的结果。其一,少数高端从业者保留自治空间与高薪酬,形成"礼宾式"或"定制式"的服务,只对愿意或能够支付溢价的用户开放。其二,广大公众接受标准化、平台化和自动化的替代方案,获得的是廉价但瘪小的情感回应或"假连接"。社会不平等由此在公共关怀与教育层面被固化:有钱人可以获得高质量的连接性劳动,弱势群体则被分配到算法与脚本化流程中。 这种分化在现实中并不遥远。医疗领域已经出现所谓的"礼宾医疗"与"零散化远程护理"的并列:某些私营医疗机构提供全天候医生、深入随访与跨专业团队支持;而公立医院与基层诊所则在人员短缺与绩效考核下,用短时咨询、电子问诊与快速结算来处理大量病例。
教育领域中,精英私校强调"导师制""人格教育"和小班教学,而公立系统在课程标准化、考试导向与在线课程压缩下,教师被迫减少与学生的情感联结与个体化辅导时间。平台心理健康产品宣传"随时陪伴"但常常由未经监管的辅导人员或自动化对话承担主要交流任务,真正的心理治疗资源则更显稀缺。 对劳动者而言,连接性劳动被降格带来的后果是复杂且双向的。情感负担的增加与控制程度的提升并存。某些岗位在被"脚本化"后仍需承担情感劳动,但却丧失了应有的判断权与劳动尊严。这种情况会引发职业倦怠、自我价值感受挫并加剧员工流动性。
另一方面,当工人通过自组织、争取规范化工作时,他们又面临技术与资本方的反击,诸如绩效算法的透明度缺失、裁员与外包策略、以及劳动立法的滞后。 那么,如何遏止或逆转连接性劳动的降格趋势?单一的技术乐观或市场自我修复显然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需要的是多层次的制度、组织与文化变革,既要保护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也要重建公共对照护功能的投资路径。首先,工人组织与行业工会仍是重要的基础力量。通过集体谈判争取更合理的工作量标准、明确的职业定义与对算法决策的透明监督,工会能够为连接性劳动者争取时间与资源,从而保证他们有空间去做真正有质量的连接工作。历史与当代的案例表明,教师联合罢工、护士争取安全护士比率、家庭护理员的组织化,都是提升服务质量与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有效途径。
其次,公共政策必须承认连接性劳动作为公共物品的属性,并相应投入。对教育、医疗与社会照护的长期投资,包括更合理的师生比、社区护理网络的扩展、以及对心理健康服务的普及化资助,都是抵御市场化挤压的重要手段。政府可以通过制定最低服务质量标准、补贴基层人手、以及对私营平台服务实行合规监管,来阻断"礼宾化"与"廉价化"的两极化路径。 第三,技术治理与伦理设计要与劳动权益并行。人工智能与数据化管理并非天生是敌人,它们可以成为增强连接性劳动的工具,但前提是这些技术设计以增强劳动者的判断与职业自主为目标,而非替代或监控。推进算法透明性、用户与从业者的知情同意、以及可解释性机制,能让技术成为支持而非掠夺性的力量。
同样重要的是,公共领域的技术应当开放、可审计,并且由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治理,而非由私营企业独占。 第四,需要在社会文化层面重塑对连接性劳动的价值认知。当前许多决策者与投资者更愿意将资源投向可量化的产出,而忽视日常交往的"不可见产出"。教育公众理解连接性劳动对社会健康、犯罪率、经济稳定性以及公民信任的长期贡献,有助于在政治上为此类投资争取支持。媒体、学术和社会运动可以共同推动这种价值重估。 最后,企业与管理层也可以采取负责任的实践:给予员工更多决策空间,取消不必要的打分与监控指标,将绩效评价纳入专业判断和同行评审中,设计合理的工作强度和班次以降低职业倦怠。
某些先行组织证明了以关系为核心的组织设计能够同时提升员工满意度与客户效果,但这通常需要突破短期利润导向的财务逻辑与拥抱长期社会资本积累的视野。 连接性劳动的未来并非注定走向退化。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伴随了劳动形态的重塑,但也为新的组织与政策创新提供了契机。关键在于社会能否在制度层面为人际关系的劳动赋予更明确的权利、资源与尊重。若能把握这一点,就能避免照护与教育被简化为肤浅的用户体验或低成本流程,进而维护一个更具包容性与韧性的公共生活。 保护连接性劳动并不是一种逆时代的浪漫,而是建设长期稳定社会经济的现实选择。
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非不可逆。通过工人组织、公共投资、技术伦理治理与文化价值重建,社会可以为连接性劳动争取回更多的时间、资源与尊重。只有这样,个体在面对痛苦、学习、衰老与失落时,才不会被留在冷漠的算法后面,而是能在真实的人际连接中找到安全、意义与共同体的力量。 未来的政策讨论应把连接性劳动放在核心位置,将其视为社会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并纳入预算与立法优先级。学者、工人、决策者与普通公民都应参与对话,共同制定能够防止去技能化与分层化的路径。资本并非全能,人民有能力并且应该掌握塑造劳动未来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