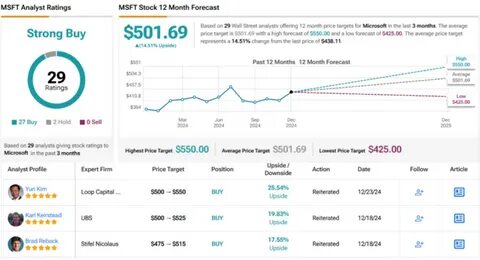全球航运业作为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来源之一,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减排压力。近年来,绿色能源技术快速发展,氢能因其清洁高效的特性成为航运业探索的重点燃料方向。在此背景下,液态氢驱动短途渡轮的实践意义逐渐凸显,尤其是挪威MF Hydra渡轮的成功运营,成为行业内的重要里程碑。液态氢为何成为短距离船舶的理想动力选择?它与电池驱动和其他替代燃料有何区别?本文将展开详尽解析。 传统电池动力渡轮已经在多条短程航线上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例如,挪威的Bastø Electric渡轮能够输送600名乘客,航程约10公里;丹麦的Ellen渡轮更是在单次充电下完成了92公里的长距离航行。
电池驱动的优点显著,如避免尾气排放、运行稳定且技术相对成熟,适合载客量较小且航程不长的船只。然而,电池存在能量密度有限、重量较大、充电时间长等固有限制,使其难以满足部分中等载客量和航程的需求。 相比之下,氢能源尤其是液态氢凭借其高比能量优势,为中等规模及中距离船舶提供了新的可能。氢的重量能量密度远高于传统燃料和电池,虽然其体积能量密度较低,但通过液化处理,氢燃料的储存体积得以最大限度减小,使得在有限船舶空间内搭载足够燃料成为现实。液化氢以其零碳排放的环保特性,也契合全球航运业向碳中和转型的长远目标。 液态氢的生产和供应同样是挑战所在。
大规模绿氢电解制备设施尚未广泛普及,物流链条复杂且能耗较高,尤其是需在极低温下保持氢的液态状态,带来设备维护及安全方面的严格要求。液氢运输中的“气体挥发(boil-off)”现象,不仅导致燃料损耗,还可能造成氢气泄漏,间接影响温室气体排放水平。这些技术和安全风险成为推广液氢动力船不可回避的难题。 挪威Norled公司运营的MF Hydra渡轮,作为全球首艘液态氢动力船,其路线仅约4至5公里,理论上完全可由电池驱动完成。然而,Norled坚持采用液氢动力,这背后有复杂的市场与技术动因。一方面,液态氢动力展现了未来中等载客和航程船舶的绿色动力潜力;另一方面,液氢供应主要依赖德国Linde公司的生产与运输网络,尽管Norled期望未来能实现本地液氢生产,但目前无相关设施,这反映出液氢产业链在地理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上的不均衡。
Linde公司在德国Leuna化工园区设立24兆瓦电解制氢厂,计划采用质子交换膜技术生产绿氢,但受供应链瓶颈及技术延迟影响,始终未完全投产。尽管如此,Linde仍向MF Hydra供给所谓“清洁氢”,其真实来源是否完全绿色尚不清晰,业界对此保持审慎质疑态度。液态氢长距离多段运输引发的能耗和排放问题,也是公众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在冷链管理和安全事故风险方面存在不确定性。 液氢驱动渡轮相比传统燃料船舶,虽然实现零尾气排放,但从电力转化为氢气、液化、运输、燃料电池再转化为机械能,必然存在多重能量损耗。整体看,其能效低于直接电池驱动方案,短距离航线使用液氢动力的必要性和经济性备受质疑。然而,液态氢动力船通过示范应用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和管理经验,为未来中长距离、更大型船舶绿色替代方案铺设基础。
此外,其他替代燃料如甲醇和氨也在航运领域被探索。甲醇生产链相对成熟,且属于液体燃料,在能量密度及发动机兼容性上具备优势,但需碳源支撑,并非全然零碳燃料。氨作为无碳燃料,其能量密度和运输便利性受到关注,但技术尚处实验阶段,氨燃烧带来的氮氧化物排放及其高毒性风险也限制了快速推广。相比之下,氢燃料在环保性能上具备根本性优势,若相关技术和供应体系完善,未来极具发展潜力。 液态氢驱动短途渡轮的实践也折射出欧盟及挪威绿色航运政策和产业布局的复杂现实。由于区域能源资源与基础设施差异,液氢产业链跨国协作成为必然,既带来合作机遇,也加剧监管协调和供应安全的挑战。
挪威拥有丰富水电资源,理论上适合绿色氢制造,但液氢制备设施的缺乏,使得初期不得不依赖德国供应。这种跨境能量流动呈现全球能源转型中的新局面。 总体而言,液态氢驱动的短距离渡轮从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角度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它证明了未来绿色航运多样化动力路径的可行性,为解决中等距离及载客量船舶的能源困境提供了一种有益探索。未来电池技术持续进步可能进一步扩大短途电动船舶的应用范围,而大型远洋船舶更可能采用甲醇、氨等燃料完成能源转型,中型船舶段的液氢动力有望在政策支持和技术革新加速的情况下切入市场,形成补充甚至核心力量。 关注液态氢渡轮的发展不仅是关注一项新技术的应用,更是探索清洁能源如何参与全球航运减碳,推动国际物流链绿色发展的重要窗口。
随着技术成熟度提升、供应链完善和成本下降,液态氢动力船舶有望在未来航运格局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助力实现全球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未来几年,该领域的政策动向、产业合作和技术突破将成为观察绿色航运产业变革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