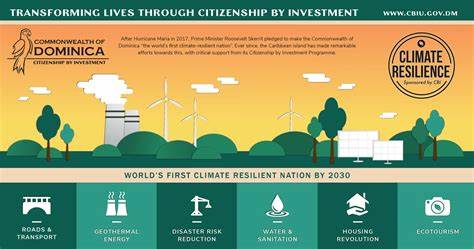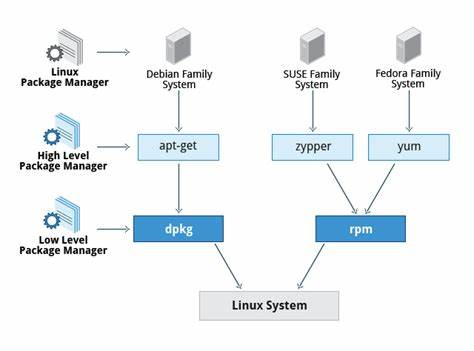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气候韧性成为社会各界广泛讨论的焦点。然而,所谓的气候韧性和适应策略是否真能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这种逐渐成为主流的应对方式背后是否存在被忽视的危机和陷阱?温室气体减排与气候适应这两大战略长期以来相辅相成,但近期趋势显示,富裕国家普遍倾向于更强调适应措施,试图通过技术升级与基础设施改造“管理”气候风险,却未能从根本上遏制气候变暖的进程。适应策略为何会成为当代气候话语的主流?这背后不仅反映出政治上的惰性,更反映了经济体系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深层结构性问题。富裕国家对根除温室气体排放的积极性不高,偏向以防洪墙、耐旱农作物培育和人口迁移等应对举措作为替代方案,试图把气候变化视为一项可以“管理”的风险,进而避免对既得利益的挑战。这种策略给人一种错觉:气候变局是可以通过技术与政策手段调适的自然波动,灾难的发生是可以避免的局部事件。然而,事实远非如此。
全球南方国家如孟加拉国、莫桑比克、马绍尔群岛等地,早已经历了气候灾害的严酷冲击,这些地区的居民被迫面对生存空间的丧失和文化的瓦解,适应策略对于他们往往意味着无奈的撤离和生命的流离失所。贫穷国家被当作气候变化副产品的“牺牲品”,其痛苦与损失被富裕国家忽视或轻描淡写,形成道德上的失职与全球气候不公。历史上类似的剥夺与冷漠屡见不鲜。1938年,英国首相张伯伦以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陌生为由,姑息纳粹政权,结果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如今,气候危机语境中,全球南方被同样边缘化,被视为“遥远的他者”,其气候遭难难以撼动国际政治的决策意志。以马绍尔群岛为例,海平面上升已使相当部分国土淹没,居民面临永久迁徙的可能,这里适应的内涵不再是基础设施升级,而是意味着祖辈留下的家园的永久消失。
在此背景下,富裕国家并未为重构全球气候策略而作出实质性改变,适应策略逐渐变成一条“避免直面现实”的捷径。另一方面,气候灾害的边界日益模糊。席卷欧洲的洪涝、干旱,英国遭遇的极端热浪,美国海岸线城市面临的水淹威胁,均表明气候变化已不再是发展中国家的专属灾难。这种现实戳破了富裕社会自我优越的假象,也揭示了适应策略的双重标准:他们愿意为气候风险买单,却难以接受为自身土地的放弃做准备。适应的面纱掩盖了更深层次的社会政治矛盾,成为推迟应对并规避责任的策略工具。气候适应不仅是一种物理上的调整,更牵涉到人类健康和社会福祉。
最新研究发现,洪涝灾害后心血管病、糖尿病、呼吸系统疾病的住院率显著升高,持续数月甚至更久,显示出气候事件带来的连锁健康危机。单纯依靠适应措施,难以解决气候变化带来的复杂健康和社会问题。经济层面,依赖适应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等。富裕国家能够承担昂贵的基础设施更新、保险和应急财政支持,而贫困国家却常常缺乏资金和技术资源,深陷灾难循环。他们历史性地对气候变化贡献甚微,却饱受其苦,而富裕国家的逃避助长了这种不公。技术解决方案,诸如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项目的快速发展,也不能简单等同于气候正义。
以墨西哥瓦哈卡地区为例,大型新能源项目未经过充分的社区协商,导致土著居民土地被剥夺。智利阿塔卡马沙漠的锂矿开采因水资源紧张而威胁生态和社区生计。低碳转型如果缺乏伦理原则和社会参与,仅能复制过去的资源掠夺模式,难以营造真正的可持续未来。历史亦告诉我们,科技进步无法自动消除政治和社会的根本矛盾。正如核武器未能消除战争根源,气候适应和绿色技术也无法终结人与自然的剥削关系。要实现气候危机的根本转折,我们必须直面不适,重新审视现行的经济与社会体系。
走向减缓为核心的策略,需要放弃增长至上的信仰,倡导符合生态与社会公正的“减增长”理念。唯有如此,减缓才能重拾应有的位置,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中心议题。否则适应将成为掩盖现实的幌子,是对受灾社区甚至全人类的背弃。气候韧性如果沦为对变局无视的幻象,那我们注定在劫难逃。只有以伦理责任和集体行动重新推动减缓策略,投入系统性变革,才能实现一个真正宜居、正义的地球未来。否则,我们就只能注视着气候灾难洗劫我们的家园,却无力阻止眼前的崩溃。
彼得·苏托里斯以环境人类学视角警醒世人:气候适应不是终点,拒绝面对真实危机的态度,是最危险的幻觉。未来的气候对策,必须将减缓与适应有机结合,并基于公平原则推动全球合作,打破固有利益的阻碍,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与自然共存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