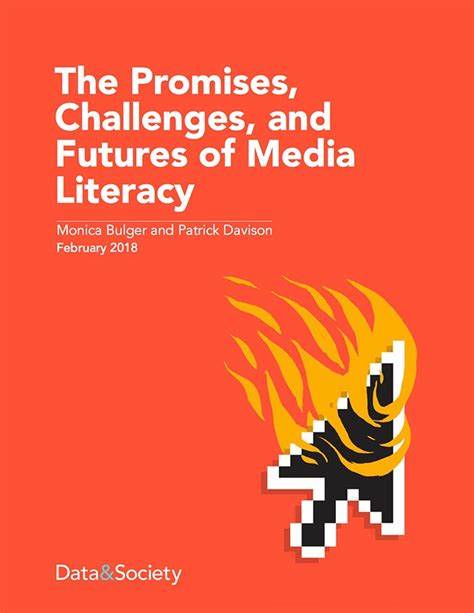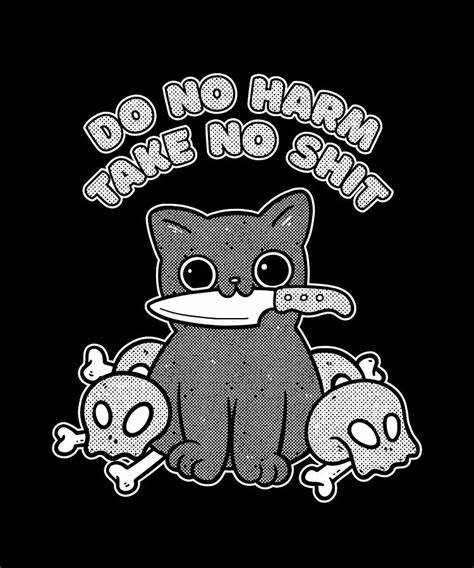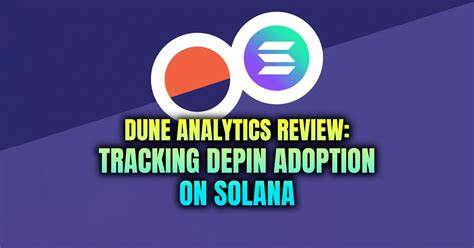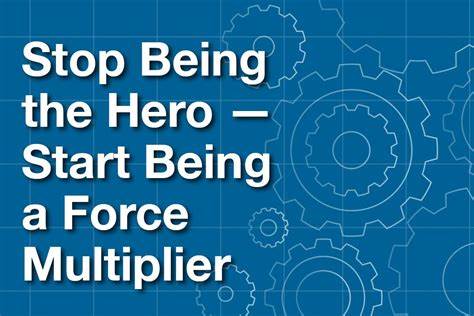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媒体素养成为公众、教育者乃至政策制定者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媒体素养的意义和挑战?媒体素养不仅仅是教会人们鉴别真假信息,或是在不同新闻来源中区分立场,更深层次地,它牵涉到知识的本质、认知框架的差异,以及社会文化中的权力关系。媒体素养的推广过程中存在许多复杂性,若没有深入剖析,反而可能适得其反。媒体素养的初衷是提升公众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使个体能够主动探究、质疑所接收到的信息,包括创作和传播的内容。正如知名媒体研究学者Renee Hobbs所定义,媒体素养要求人们“主动询问和批判性思考所接收和创造的信息”。这是一项赋予个人权力的技能,旨在支撑民主社会的健康运行。
然而,对于媒体素养的具体实施,尤其是在教育体系中的落地,却往往停留在表层,比如简单地教导学生区分不同新闻频道的偏见,或者在技术使用上告诉他们“不要全信维基百科,要用谷歌”。这些做法显然无法满足当代多元复杂的信息环境需求。事实上,某种扭曲的媒体素养理念已经存在多年,学生们被要求辨别由不同政治背景的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同时面对“不信任维基百科”的刻板说法。他们的批判思维更加局限于二元对立的事实与谎言的游戏中,而缺乏对更深层次认知模式的理解。媒体素养被频繁提及作为解决“假新闻”问题的灵药,受益人包括资金提供方、新闻媒体公司、政界人物以及社交媒体巨头。他们多半主张识别宣传、理清信息来源、学会事实核查等技能,但背后常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偏重于批判某一政治阵营的内容。
这样不仅无法弥合社会的政治分裂,反而可能加剧对立。根本问题在于,当前的信息战争其实是一场认识论的战争。我们所争论的,已不只是事实的真伪,更是人们如何认定何为“真理”。这使得“事实”这一概念变得更加不确定和多元。不同社群基于其固有的文化背景、经验及信仰体系,对于何为可信、何为真实有着不同解释。例如,保守福音派社区往往用对圣经的诠释来理解政治言论,而非字面真相。
土著社区更依赖经验和口述传统,而非西方科学方法。这些多样化的认知模式对媒体素养教育提出重大挑战。媒体素养不能仅仅停留在教人辨别新闻报道中事实与偏见,更应关注不同知识体系之间的鸿沟与辩证关系。否则,媒体素养可能沦为权威认知体系对其他认知方法的排斥和统治工具,反而加剧信息的极化和认知割裂。此外,媒体素养教育的政治环境亦值得反思。许多媒体素养倡导者出于对某些保守媒体和现象的担忧,将教育目标聚焦于揭露如“另类事实”或宣传机器,但很少关注政治分裂背后认知世界的多样性。
这种单一视角很难让学生真正理解复杂信息,也不利于培养包容性和同理心。实际上,人们对信息的接受往往与其情感认同和心理需求紧密相关。许多发布明显误导甚至谣言信息的人,往往清楚其真实性存疑,甚至并不在意真伪,而是通过传播表达身份认同或政治立场。这一现象说明,理性事实核查和批判思维的灌输,不能单纯依赖认知层面,更需理解人的社会心理机制。网络环境的开放性和匿名性给各种信息传播和认知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些团队巧妙地将怀疑主义和批判性思维作为武器,通过有意提供模糊和冲突的信息,摧毁传统权威认知结构。
例如俄罗斯国际电视台RT的宣传口号“多问为什么”,鼓励观众质疑权威信息。虽然这一态度在教育中倡导批判性思维时看似合理,但在缺乏坚实事实基础和理性引导下,容易被利用为转移焦点甚至传播虚假信息的工具。此外,社交媒体几乎无限地放大了信息传播速率和范围,却缺乏有效的内容审核及编辑机制。这使公众在需要自我甄别信息的责任和压力日益增大。在认知多元、极端个体化和社会分裂并存的现实中,单靠传统的媒体素养教育难以奏效。误导性信息背后的“传播者”并非普通信息消费者,他们多是非常熟练的数字传播者,掌握从表情包到视频剪辑的各种工具,能够操纵舆论、触发情绪甚至煽动冲突。
现实中,教育中的媒体制作培训让更多人具备参与数字传媒的能力,但使用目的多样,其中不乏极端言论和排他性观点的传播者。这不禁令媒体素养教育者深思:技能的传授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善的传播。我们需要思考更深层次的教育目标。媒体素养教育应更加关注认知心理和社会文化背景,培养对于不同知识体系的理解和尊重,而非单一的事实检验能力。除了提升认知能力,更需要加强同理心和跨文化理解能力,认识到不同社会群体对信息和真相的多样解读。媒体素养还应促使人们反思自身的认知偏见,如确认偏误、选择性关注等,从自身出发识别信息误导的机制,而非单纯责怪外界。
现实案例中,有些青少年因在网络上对一个事件进行自主探索,最终陷入极端意识形态团体的圈套,甚至导致悲剧。这警示我们,媒体素养教育不能忽视心理健康和社会环境对认知选择的影响,需要联动社会支持和心理辅导机制。面对这一切,教育者应鼓励学生建立“认知免疫系统”,即了解自身如何被信息误导,掌握分辨真伪的工具和心态。但要警醒的是,纯粹依赖理性解释对抗情绪和认知偏差的做法有限,人们更愿意相信符合自身认同和情感的故事。为此,教育应助力学生理解并构建多元视角认知结构,既坚守自身理性立场,也包容甚至冷静分析对立观点的形成逻辑。培养一种能够在对话中保持距离和批判的能力,既不过度情绪化,也不过度机械思考,是一项极具挑战的任务。
如今,信息环境只会更加复杂,媒体素养的未来应是以网络理论为基础,分析信息在动态社会网络中的传播与接受模式,关注网络的社会结构如何塑造知识获取,并设计跨学科的教学方法涵盖认知科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唯有如此,媒体素养才可能真正帮助人们在后事实时代,辨别真谛,抵御操纵,维护社会对话和理解。总的来说,媒体素养远不只是“分辨真假信息”的技能,它是一场认识论的革命,也是情感和社会认同的挑战。教育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能单靠传授标准化技能解决问题,而应引导学习者深入理解自身和他人的知识构建方式,既理解媒体信息的生产机制,也明白认知差异带来的认知冲突。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这个信息复杂且被操纵的时代,培养出既理性又包容,既批判又开放的新时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