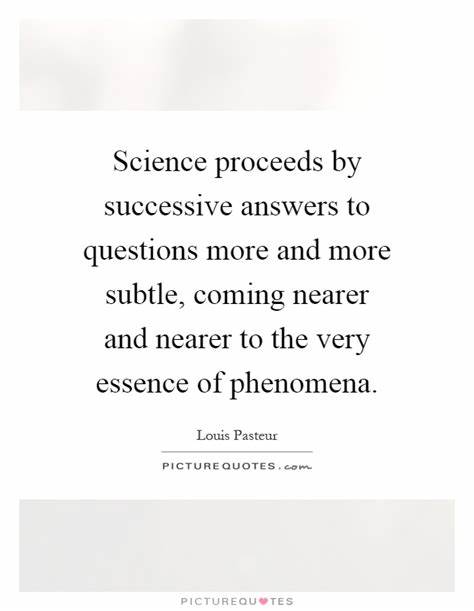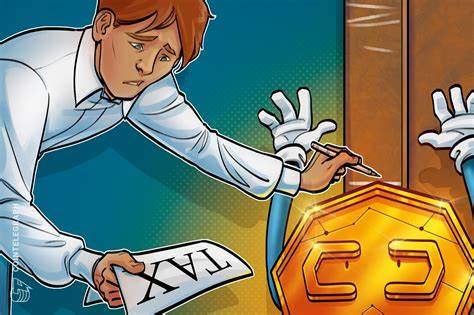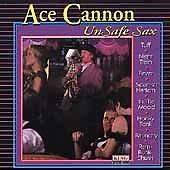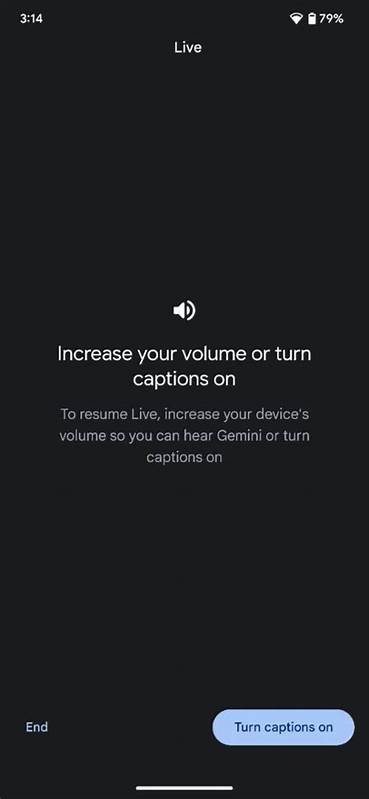科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无数令人惊叹的发现和理论突破,但这些伟大的进步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始于科学家们对某些重要问题的深入思考与质疑。历史和哲学家指出,科学推进的真正动力往往不是技术的革新,而是科学家提出有针对性、可引导研究方向的关键问题。这些问题像灯塔一样,引导着对未解之谜的探索,最终促成新的知识体系的建立。以自然选择理论的诞生为例,达尔文与华莱士分别独立提出的进化论,展示了问题驱动科学的魅力。达尔文早在20世纪初开始沉思物种起源的机制,但真正激发他行动的,是华莱士在1858年发表的论文,这篇论文直指“物种形成变异的趋势”。华莱士的出现对达尔文而言既是警示也是动力,迫使他加速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因此诞生,成为生物学史上一块里程碑式的基石。生物学家恩斯特·梅尔(Ernst Mayr)在其著作《生物思想的成长》中深入探讨了这一历史现象。他指出,尽管达尔文和华莱士走上了相似的理论路线,但他们问的问题本身是极为独特和深刻的。在科学史上,能有不同个体在相近时间内独立提出类似理论,说明有些问题已经成熟到需要被回答,而科学发展正是顺应了这一内在需求。梅尔认为,发现科学重大理论的关键不在于竞争,而在于“提问者”与“回答者”的关系。科学家在面对茫茫数据和现象时,通过提出恰当且富有洞察力的问题,将复杂的现实分解为更易理解的范畴,推动研究的深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和华莱士虽然借鉴了当时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的著作,但莱尔本人持有本质主义和创造论的观点,反对生物进化。即使如此,莱尔提出的关于物种为何灭绝或起源的疑问,为达尔文确定研究方向提供了启发。这里体现了提问的力量,有时问题本身的价值超越了提出者的答案,激发后人寻找更准确的解释。科学史中,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许多先驱者提出了错误的理论,但因其提出了重要的问题,促使后续学者在质疑与修正中走向科学真理。正如梅尔提到的,美国生物学家戈德施密特提示的全系统突变学说虽未被采纳,但激发了对物种形成的新思考。
这种“错误的答案”反倒成为新理论的催化剂。问题提问的重要性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与历史研究领域也同样显著。以罗马帝国战略研究为例,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的《罗马帝国大战略》一书,尽管由于论据缺乏科学性饱受批评,却因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战略问题,引发学界持续的探讨和反驳。由此诞生的研究成果丰富了该领域,说明即便错误观点中隐藏的疑问,仍可导致知识体系的扩展。当前学术界存在一个普遍问题,那就是文化倾向于奖励答案的发现,而忽视提问的艺术。许多研究者花费大量精力重复解决已被提出,却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导致学术成果同质化且局限。
真正推动学术进步的往往是善于提出新颖且深刻问题的科学家。然而,培养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尚无成熟的方法论,这成为当代科研教育的盲点。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大型语言模型(LLM)的普及,这种状况有望被改变。有效利用这一类工具,关键在于如何提出明确、有针对性的问题。人们发现,通过不断优化问题的表述,可以促使人工智能生成更具深度与创造力的答案。未来,这一过程可能反哺人类,促使年轻一代学者学会从不同角度审视问题,发展出更为精妙的提问能力。
科学作为人类认识自然和自身的旅程,并非一蹴而就。它是一阶梯式上升,每一次跨越都由先前提出的疑难问题指引方向。没有问题的提出,也就没有知识的答案。从莱尔、达尔文到现代研究者,科学发展证明了提问的力量和价值。我们应重视这一传统,致力培养提问能力,因为好的问题是打开未知世界的钥匙,是推动文明进步的引擎。面对未来复杂多变的科学挑战,唯有不断提出尖锐、开放和创造性的问题,才能激发持续创新与发现。
正像有人所言,科学正是“一次仅解决一个问题”而逐步迈向真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