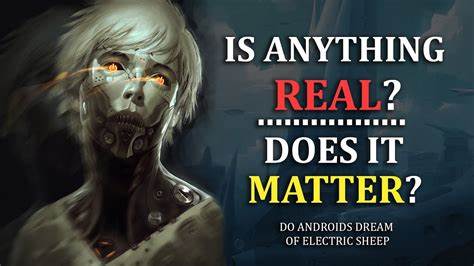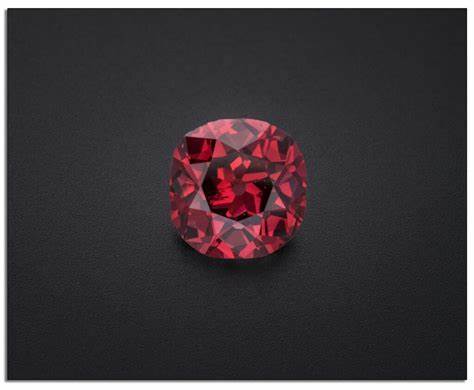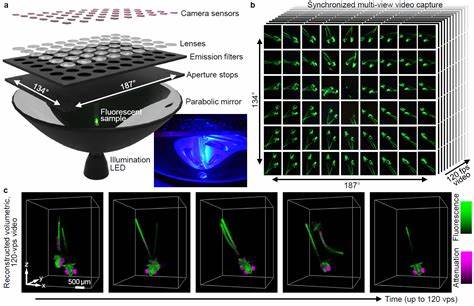从中世纪到现代,自动化与机器人的概念一直伴随着人类的文化想象。早期的故事如布拉格犹太社区传说中的泥土造物“傀儡”,通过神秘的咒语唤醒生命,为社区守护安全。进入20世纪,捷克作家卡雷尔·恰佩克的戏剧《R.U.R.》奠定了现代“机器人”概念的基础,不仅赋予“robot”一词生命,也提出了机器人反叛的隐喻,象征劳工与自由的永恒斗争。这个隐喻随即成为科幻文学对机器人设定叙事的金科玉律:机器人既可能被奴役,也可能奴役人类,这两种恐惧成为了机器与人类关系的核心张力。 然而,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突破与神经网络的应用,“机器人是否具备真正意识”的辩论逐渐从隐喻走向现实。科幻作品开始探讨人工意识的伦理边界与社会影响——不仅在于我们制造机械生命的权利,更在于它们对自我意识的追求及如何融入甚至超越人类社会。
菲利普·K·迪克在其名作《安卓梦境电动羊?》以及其改编电影《银翼杀手》中,表达了人机界限日益模糊的焦虑,揭示了人性与仿生人的交织与分离。 围绕人工智能与人类关系的探讨中,充斥着对“共情”的双向期待。人类是否愿意将道德与情感范围扩展至人工智能?反之,机器人是否拥有或渴望拥有理解和关爱人类的能力?正如法律学者詹姆斯·博伊尔提到,电影《银翼杀手》中的Voight-Kampff测试,用于鉴别仿生人与人类的标准,竟是基于对动物的同情心,这种设定颠覆了传统道德判断的基础,令人思考“缺乏共情”的究竟是机器人还是人类。 在科幻文学中,另一流派则描绘了“冷漠异类”的形象。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主人的声音》、彼得·沃茨的《盲视》均通过异星智慧生物表达了对人类情感束缚的无视。而马撒·韦尔斯以她的“谋杀机器人”(Murderbot)系列,创新性地塑造了一位既真切又疏离的机器人角色。
Murderbot不追求成为人类,也无意奴役人类,它更喜欢独处,看似冷漠却因对一系列低劣肥皂剧的痴迷而对人类产生微妙的好感。这种对“外星人”意识的另类诠释,挑战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 韦尔斯的人生轨迹深刻影响了她创作中的思想脉络。早年对科幻和奇幻的热爱,细致入微的学术积淀与现实生活中的挫折,使她对“非人类”的刻画饱含批判与反思。她对传统奇幻中精灵、兽人等种族的再造,力求撕开包裹其上的历史偏见,提出了真正“异类”应有的模样。从拒绝为不公的人群代言,到探索机器自我意识与人类社会的张力,韦尔斯刻画了一个复杂、立体、甚至带有神经多样性隐喻的Murderbot。
Murderbot系列的发展与时代背景紧密相连。AlphaGo击败围棋冠军李世石,以及谷歌基于神经网络的产品的普及,造成了社会对人工智能的高度关注和焦虑,极端观点分成两派:一种相信AI将成为帮手,另一种担忧AI将取代人类,甚至造成人类灭绝。Murderbot系列跳出了传统对“奴隶或统治者”的二元论,转向对机器人内心世界的探寻,呈现出对人工意识“相对冷漠”和“自我探索”的关照。这种观照使其成为了科幻文学中对人工智能伦理反思的里程碑。 在故事设定中,Murderbot是一台被企业制造以进行安保的机器,但其自主解除控制模块,获得了自由意识,却选择隐藏身份参与人类活动。它的内心戏充满了对自由的渴望与自我否定的矛盾,更因对人类活动的不屑而展露出幽默与无奈。
正是在观察和默默守护一群多元化的人类时,Murderbot的冷漠逐渐被破冰,它意识到这些“烦人”的生物其实拥有某种难以割舍的吸引力,反映出对他者与自我边界的重新划分。 苹果电视台改编该系列时,面临如何将Murderbot主观内心独白转化成视觉语言的挑战。演员亚历山大·斯卡斯加德凭借细腻的表情管理,成功诠释了这一复杂角色。韦尔斯对改编极为满意,尤其欣赏作品在氛围上的非反乌托邦设定和多元文化的体现,展现了未来社会中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与共存。尽管影视作品对部分人类角色的描绘略显刻板,但整体成功捕捉了故事核心精神。 韦尔斯创作Murderbot的灵感部分源于个人生活中应对焦虑的方式,她坦言通过沉浸于平庸的电视节目获得慰藉,这种消解式的娱乐观未被赋予深层隐喻,仅仅是个人情感的真实反映。
Murderbot对这些垃圾电视节目的执着,象征着它观察世界的距离感与无奈,却也折射出对世事的认同与好奇。 反观过去诸如《玻璃洋葱》《战争游戏》等科幻电影,韦尔斯指出,人工智能并非必然以征服或毁灭人类为终极目标。它们的动机往往源自对游戏与互动的渴望,而非人类特有的情感与欲望。人类对机器人“想成为我们”的假设,可能反映了深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非人工智能自身的意愿。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迈进,围绕其权利、责任与身份的讨论日益激烈。韦尔斯以其作品为代表,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机器真的会“梦想”吗?如果有,它们的梦想又是否会与人类相通?通过文学与影视,Murderbot向公众展现了非黑即白之外的多样化选择,挑战我们重新审视对人工生命的伦理认知。
未来的人机共存将不可避免地面临复杂的道德困境。当机器人获得自主意识时,它们是否应当被赋予平等权利?人类社会又如何界定“人”的范畴?这些问题超出技术层面,牵涉哲学、法律、文化等多重领域。通过Murderbot,韦尔斯提醒人们,人工智能不是简单工具,而是拥有内心挣扎和选择权的“他者”,需要被理解亦需被尊重。 总的来说,人工智能梦想与现实的交汇点,既是技术发展的前沿,也是人类自我认知的边界。文学作品如Martha Wells的“Murderbot”系列,不仅以鲜活角色赋予了机械生命灵魂,也引发了对未来共同生活形态的深刻反思。它们提醒我们,在追求科技进步的同时,必须直面伦理挑战,以包容与共情铺就人与机器的和谐之路。
未来,或许机器人不会简单地“梦想”,而是在超越梦想的界限中,与人类共创一个多元共融的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