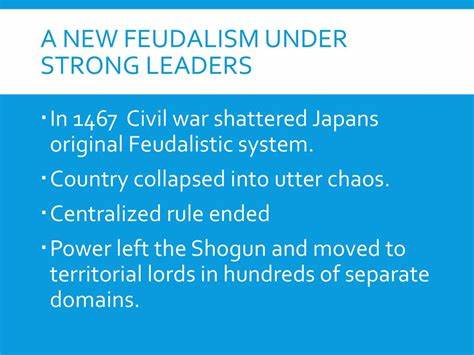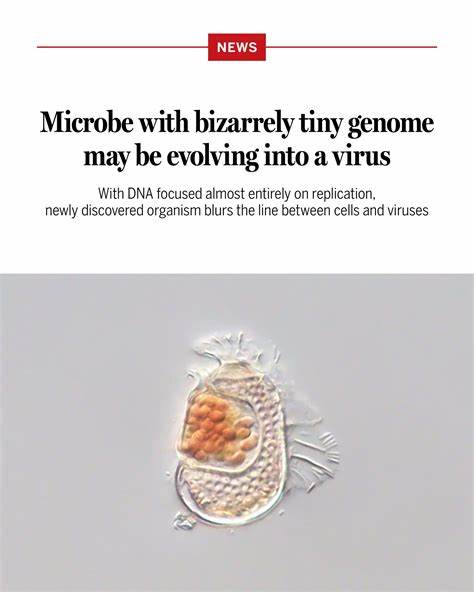20世纪60至70年代,日本极左运动经历了一段波澜壮阔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历史阶段。与全球1968年浪潮相呼应,日本的激进左翼不仅对美国霸权和日本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抗争,也在自身内部爆发了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内战。这场极左内部的分裂与集中之间的矛盾,无论是从历史意义还是理论层面,都为当代革命运动提供了宝贵的反思素材。本文将以日本新左翼的起源、激烈的内部争斗以及所谓的“联合赤军事件”和“内战”现象为脉络,探寻分裂与集中二元动力在极左运动中的表现及其根本原因。 日本极左运动的形成离不开19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两个重要根源组织——从日本共产党分裂出的共产主义同盟(BUND)与革命共产主义同盟(Kakukyōdō)。其中,BUND激进反对日本共产党的和平主义路线,强调通过直接行动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并在1960年反安保斗争中发挥了带头作用。
BUND通过群众动员震撼了日本政治舞台,尤其是在这场反对美国与日本签订安全条约的运动中激发了以学生和工人阶层为主体的基层力量。然而,运动进入关键阶段时,群众自发暴发的力量迅速脱离原有组织的控制,形成了规模空前的分散与动荡。 与BUND不同,Kakukyōdō成立于1957年,由知识分子领导,主张建立一个革命党,有别于传统左翼政策。这一团体的理论基础融合了京都学派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的“场所逻辑”及现代科技理论,意图用高度集中的党组织作为革命的核心力量。Kakukyōdō与从BUND分裂出来的派系发生了复杂的交织,最终在1963年分裂成核心派(Chūkaku-ha)与革命马克思主义派(Kakumaru-ha),反映了围绕组织形式、革命任务和动员策略的根本分歧。 1960年代反安保运动之后,新左翼的激进道路逐渐清晰。
Chūkaku-ha勇于直接参与激烈街头战斗,主张武装革命和针对国家机器的激进斗争,吸引大量年轻激进分子。与此同时,Kakumaru-ha虽然同样激进,但更强调意识形态统一和党内纪律,倡导高度集中的党组织以确保革命纯洁性。两派的路线差异不仅在街头表现为暴力冲突,更在理念上反映了革命“集中”与社会运动“分裂”之间的张力。 1970年代,日本极左内部暴力事件频繁爆发,其中尤以“联合赤军事件”与派系间的内战(uchigeba)为代表。联合赤军(URA)的形成,是试图将分散的革命派系统一成为一个具备严密军事纪律和革命意识的武装政党。然而,这种高度军事化和纪律性的融合反而导致了严峻的内部审判和残酷的清洗运动,最终造成了数十名成员非正常死亡。
这场悲剧暴露出革命运动内部对分裂的极端担忧和反应,试图“通过统一达到革命”,却惨遭失败。 Uchigeba作为极左运动内部的持续性暴力斗争,体现了派系间互不信任和排斥异己的极端情况。Chūkaku-ha与Kakumaru-ha之间的冲突尤为激烈,起因多为意识形态分歧和组织权力争夺。暴力形态包括秘密袭击、绑架、暗杀乃至校园斗争。这场所谓的“内战”不仅让日本左翼运动受到沉重打击,也让广大激进分子感到失望与疏离,严重削弱了整体革命力量。 此外,解放派(Kaihō-ha)与Kakumaru-ha之间的纷争,也反映了革命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张力。
尽管Kaihō-ha主张更为非列宁主义的工人自管理和议会外斗争,与传统的党派主义有所区别,但仍未能避免极端内耗。内部进一步分裂为学生派与工人派,产生了更加微妙的内部分裂和自我瓦解,表现出高度的混乱和断裂。 这些暴力和分裂的根源深植于极左运动面对革命组织难题时的两难处境。一方面,革命势力需要通过集中党组织的力量来统筹指导和抵御外部压力,避免过度分裂削弱自身;另一方面,运动本身的自发性、群众动力和多样性倾向于自然导致分散,甚至去中心化的状态。当这两股力不平衡时,既有“联合”遭遇惨败,也有“分裂”被妖魔化为叛徒,极端紧张的权力斗争和激烈的内部肃清便不可避免。 对此,理论家如长崎宏提出了“党意识形式”的划分,区分为“先形党”和“实形党”。
“先形党”源自群众自发的组织和行动,是革命蕴育的初级形态,无需强制的意识形态统一;“实形党”则试图通过引入外部政治程序、意识形态导向和制度化平台,将游离的群众组织转化为有纪律的革命党。这种转变过程往往充满冲突和抵触,因为它与群众的即兴性和分散性质相冲突。日本新左翼的惨烈历史正是这种张力的生动体现。 运动的悲剧同时也折射出时代的社会变迁。1960年代的日本社会正经历现代性的深刻转型,科技的发展、消费主义的兴起和社会结构的复杂化,使得传统的阶级斗争模式遭遇重大挑战。革命运动试图恢复劳动的“本真形态”,却不得不面对劳动的破碎和个人主义的兴起。
此外,对日本传统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如部落民(burakumin)的关注也成为极左内斗的焦点,进一步加剧了分裂。 总结来看,日本极左运动中的分裂、集中与内战是一场革命组织在面对群众自发性、组织需求与社会变迁时陷入的深刻困境。联合赤军事件和uchigeba的惨烈教训,提醒当代与未来的革命运动必须谨慎地处理“党”的组织形式与群众动力之间的关系。革命不应简单等同于高度集中的军事化集团,也不能放任无序的分裂和内部冲突。 此外,日本激进左翼的历史经验也启示我们,任何革命运动在迈向成功的道路上,都不可避免地要处理好集权与分散、纪律与自由、统一与多样等矛盾。懂得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尊重运动内在的张力和平衡,方能避免重蹈覆辙,开辟新的革命可能。
未来的革命组织或许需探索一种既能容纳群众自发性又具备灵活组织特色的新型结构,实现真正的社会变革而非内部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