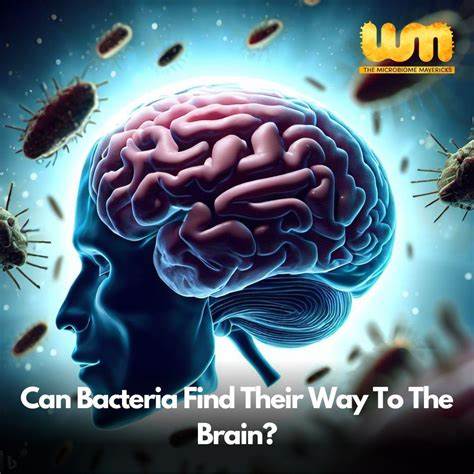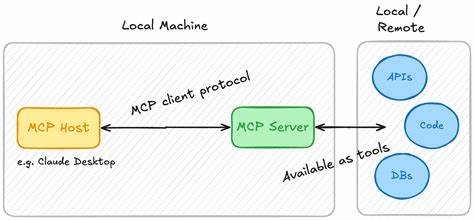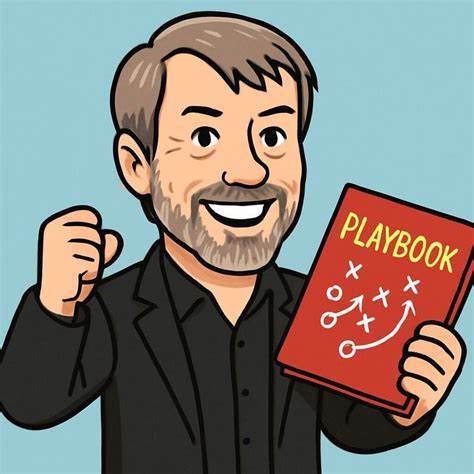历史划分,也称为历史时期划分,是史学研究中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它试图将人类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按时间顺序分割成多个相对独立、便于理解的时期。然而,真正界定这些时期的精准边界,却常引发学者之间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历史的进程并非线性且整齐划一,文明交织错杂,文化变迁渐进微妙,因此任何人为划分都带有主观色彩。对绝大多数人而言,历史学习时所接受的各种时间划分,更多是建立在习惯、传统和文化认知基础上的大致框架,而未必能完全反映全球范围的历史全貌。本文将从个人认知的角度,结合传统史学观点,讲述一种属于我脑海中对历史时期划分的自然反应和感知。
我的大脑面对不同时间节点时,自然而然地将其归入特定的历史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显著的文化、社会和技术特征,构建起一幅连续的时间地图。 古代青铜时代大约自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776年,是人类文明起步的重要阶段。文字的发明常被认为是开启“历史”记载的标志,因此将这一长时期以书写为起点尤为合理。尽管从现代视角看,这晚于实际产生的人类历史远古时期,但文字出现让人类得以记录经验、传承知识,文明开始高度发展。期间,米诺斯王宫的壮阔、苏美尔王乌尔·帕比尔萨格的统治,以及莫亨佐-达罗“跳舞的少女”等遗迹,呈现早期文明的独特风采。由此,大脑开始自然地将那些遥远的负数年代纳入“青铜时代”的概念范畴。
随后是被称为“高古代”的时期,大致跨越公元前776年至公元363年。这段时间对我而言是“真正的精华”。我自然而然选择以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作为这一时代的起点,部分原因是我个人对古希腊的文化偏好甚至超越了罗马。不可否认,希腊文化在哲学、艺术、政治制度上的成就,给西方文明奠定了坚实基础。古希腊神庙、巴特农神庙的雄伟,以及秦始皇兵马俑的壮观,成为此时期文明的标志。 介于古代与中世纪之间的公元363年至622年,被我视为一个奇特的过渡时期。
历史上所谓的“晚期古代”,在时间和文化意义上均难以归入明确的阶段。此时的罗马帝国经历分裂,古典多神教逐渐衰退,基督教成为主导信仰,社会政治结构发生深刻变革。贾斯蒂尼安皇帝的统治、维也纳迪奥斯库里德斯手稿的保存,以及大不里士凯旋门等文物正好体现这种动荡与变革。这种模糊时期在我脑中有着独立的地位,既不完全属于古代,也未曾真正进入中世纪。 进入中世纪,也被称为“黑暗时代”的时期,从622年伊斯兰教兴起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这段时间,对历史进程产生了巨大影响。穆罕默德和随从逃离麦加,形成了伊斯兰纪年元年,这一事件在我心中坚定地划出了古典时代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
在这一时期,西欧的封建制度、拜占庭的文化遗产、阿兹特克文明的辉煌以及巴格达智慧宫的学术繁荣,都构成绚丽多彩的中世纪画卷。 中世纪结束,而殖民时代应运而生,时间跨度自1492年至1776年。哥伦布横渡大西洋的壮举犹如历史的分水岭,打破了长期隔离的“旧世界”和“新世界”界限。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带来了巨大财富,也铺垫了殖民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糖业和奴隶贸易的阴影掩盖了文明互通的曙光,许多原住文化在这一时期被摧毁,却也在废墟之上孕育出新的文化形态。 克服殖民时代的桎梏后,进入工业时代,时间定位于1776年至1918年。
1776年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美国独立,但在我脑海中,这一年是詹姆斯·瓦特第一次出售蒸汽机的年份,标志着工业革命的正式开始。曼彻斯特从一个小镇迅速转变为工业巨城,这段时间不仅见证了机械化生产的飞跃,更是人类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注脚。拿破仑东山再起和明治维新也反映出这一时代各地不同文明的转变与碰撞。 最后,是我认知中的后现代时代,始于1918年延续至今。尽管二战结束的1945年常被作为现代历史的分界线,但我更倾向于将这一时代起点放置在1920年代左右。当时汽车和冰箱普及,电影和广播兴起,极权政治和文化现代性的崛起,让世界从根本上走进了另一阶段。
那时的巴黎夜店女孩与今日生活中的我们或许有文化上的隔阂,但在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核心上,却已有令人震惊的连续性。历史的不确定性在此刻似乎消融,现代世界呈现出强烈的共时性。 我大脑的历史时期划分,不仅反映了纯粹的时间逻辑,更与文化认知、社会变革及技术进步密不可分。这种主观的时间感知帮助我在面对浩如烟海的年代时,快速定位历史阶段,形成一种直观的时间地图,强化对不同文明和事件的理解。 虽然这种划分带有个人色彩,但它能够提醒我们,历史不仅是年代叠加的静态文本,更是活生生的文化体验和社会变迁。它启发我们以更加灵活、多元的视角看待历史,体认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及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通过理解自己大脑对历史的感知,我们能更好地整合历史知识,激发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层次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