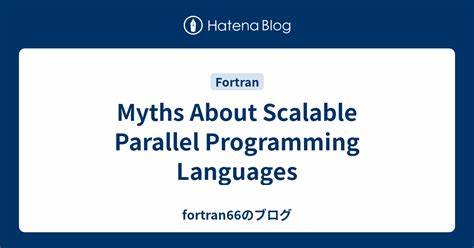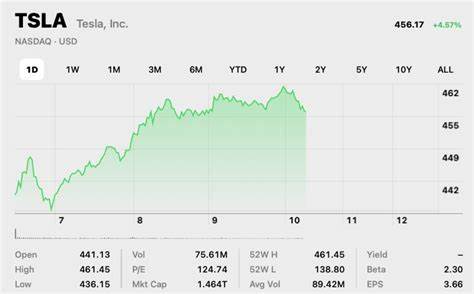近年来,随着全球社会动荡和文化迷失,虚无主义这一哲学和文化现象越来越多地进入公众视野。所谓虚无主义,往往被理解为对价值和意义的彻底否定,是一种相信"无所信仰"的状态。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尽管虚无主义本质上看似否定一切信仰,现实中的极端行为却往往伴随着强烈的信念和坚定的理念支持。为什么拒绝一切既定价值观反而会催生出极端的暴力与破坏?这背后的复杂性值得深入探讨。 美国联邦调查局近年提出了"虚无主义暴力极端分子"这一概念,指出这些肇事者的动机不仅仅是仇恨特定政治观点,而是发自对整个社会的厌弃和渴望摧毁现有秩序。与传统恐怖分子为某种信念奋斗不同,虚无主义极端分子则试图通过制造混乱和社会瓦解宣泄内心的空虚与绝望,使社会陷入无序的荒漠。
然而,正是这种绝望与无意义感,催生出一种异常强烈的信念 - - 认为只有毁灭才是寻找意义的方式。 近期,《纽约时报》知名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提出,当前美国的政治极化和文化撕裂导致某些群体转向激进虚无主义。他担忧,曾经关注传统和秩序的保守派群体,逐渐演变为彻底否定传统和价值的"激进解构者"。这种转变既反映出文化焦虑,也引发新的社会混乱。布鲁克斯更将这种趋势与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者相比较,认为历史上保守主义的僵化压迫曾催生反叛与极端主义,而今日社会似乎重演了类似的模式。 然而,对布鲁克斯观点的深入思考表明,他所描述的历史因果链并不完全贴合历史事实。
正如哲学家诺伦·格茨在其著作《虚无主义》中指出,19世纪俄国虚无主义的根源恰恰是当时社会高度保守且拒绝变革,年轻一代透过对虚假的信仰与仪式的反抗,寻求从破坏中寻找新的价值秩序。换句话说,虚无主义并非简单的信仰缺失,而是在传统信仰被剥夺意义甚至变成形式主义空壳时,对新价值的迫切渴望和极端回应。 宗教和仪式在社会认同和精神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许多人因此相信宗教复兴能够抵御虚无主义的蔓延。大卫·布鲁克斯甚至乐观地指出,更多年轻人重返教堂,表现出对"信仰的信仰"的欲望,暗示这可能是解决虚无主义的有效路径。然而,回归宗教仪式如果仅仅是为了仪式本身,缺乏真实的内涵和意义,反而可能加深内心的空虚感。十九世纪俄国年轻人正是如此被外表的仪式和传统所击败,因看不到自身信仰的意义纷纷脱离,导致极端抗争和虚无主义思想的爆发。
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在对"上帝已死"的论断中曾严正警告,盲目崇拜新的"信仰"或形式性的"信仰"并无法解决真正的虚无问题。尼采认为,人们需要从传统权威束缚中解放,通过自主的价值创造来赋予生活新的意义。相反,如果人们简单用新的"神"来替代旧的"神",依旧没有真正承担起自身生命与价值创造的责任,这只会使虚无主义继续蔓延。 与尼采类似,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也警示现代民主面临的危机。她认为,民主政治正逐渐沦为"空壳式"的仪式,人们不再积极参与政治讨论和公共决策,而是将政治责任交给官僚和政客,自己仅仅以投票的形式"参与"。这种消极的政治参与形成所谓"无人统治" - - 一种形式上存在但实际上缺乏真实责任感和参与感的权力运行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社会成员失去对公共生活的掌控,社会民主的生命力逐渐消失。
阿伦特进一步指出,现代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介入,可能加剧这种趋势。机器取代人的决策和责任承担,将加速社会向"虚无乌托邦"滑落 - - 一个人们完全无需承担责任,也无需真正参与公共事务的社会。这样的社会既非真正的政治社会,也无法为个体提供意义和归属感,反而会让虚无主义根深蒂固。 因此,要抗击虚无主义,关键不在于简单回归宗教形式或者机械守旧,而在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积极再生。阿伦特提倡基于古希腊城邦(polis)的政治理念,强调通过公共空间的交流与辩论,实现个体间的相互理解和价值共构。政治不应仅是权力斗争或官僚管理的代名词,而应成为人们赋予生命意义的场所。
只有通过真实的互动和政治参与,个体才能承担起自身生命的意义,抵御无意义感和虚无主义。 当代年轻人重新走进教堂,更深层次的原因或许是对真实交往和归属感的迫切渴望,而非仅仅盲目追求宗教仪式的表象。他们试图寻找的是一个有温度、有交流的社群,是一个能够满足心灵渴求的现实空间,而非冷冰冰的传统仪式。数字时代的虚拟社交虽便利,但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的人际连接和面面对话。这种面对面的交流正是古希腊政治生活的精髓所在,也是现代公共生活重建的关键。 总的来说,虚无主义的根源不仅仅是一种信仰危机,更是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生活的深刻反思。
试图通过宗教仪式的简单复兴来治愈虚无主义,无异于对症下药而忽略了病因。真正的出路在于重新激活政治生活,重建具有真实意义的公共空间,激励人们主动参与社会事务,承担起共建意义社会的责任。唯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突破虚无主义的困境,创造一个充满生机与希望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