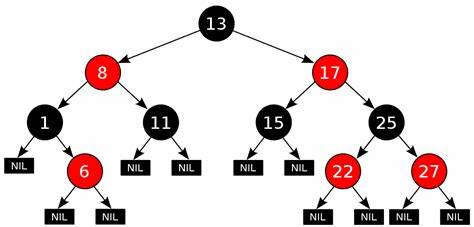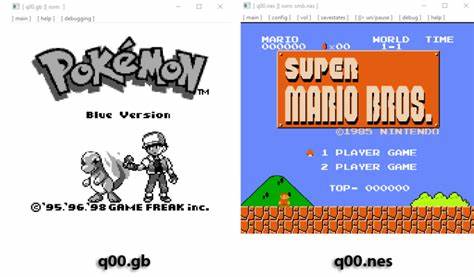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简称GenAI)的迅速发展,犹如20世纪中期聚酯纤维在纺织行业中的崛起,既带来了效率与便利,也引发了关于价值和文化意义的深刻反思。它不仅改变了创作的途径,也预示着我们文化再生产机制的深刻变革。透过聚酯纤维的历史,我们或许能更好地理解GenAI在艺术和社会中的复杂地位和未来趋势。二十世纪初,白领阶层普遍穿着棉或麻制的衬衫,这些天然纤维虽舒适,但洗后极易起皱,熨烫成为家务中繁琐的负担。直到杜邦公司通过化学研究发明出聚酯纤维,这种纤维强韧耐用,且大大降低了服装维护的复杂性,实现了“免熨烫”与“即洗即穿”的革新。1950年代,聚酯纤维代表着科技进步和生活效率的象征。
其后,包括Brooks Brothers在内的品牌推出了混纺的无皱衬衫,迅速风靡市场,改变了人们的服装习惯。可是好景不长,随着1970年代聚酯的大规模普及和工业化生产,无论服装风格还是品质都开始趋于同质化,其中尤以廉价且视觉俗艳的双针织休闲服受到广泛批评。对聚酯的文化反弹与价值重估随之而来,不止是因为它穿着舒适度的缺陷,比如透气性差易黏腻,更重要的是它所承载的社会阶层与审美定位的变迁。天然纤维如棉与麻重新焕发高贵身份的象征地位,尤其在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圈层中更为明显。1980年代,《官方优雅穿衣手册》的流行和棉花种植者联合发起的推广活动,力图将棉花重新塑造为精英文化的标志。聚酯则被冠以廉价、粗俗的标签,成为阶层歧视与审美挑剔的靶子。
当流行文化大师约翰·沃特斯的电影《聚酯》透过影像和名字唤起强烈的庸俗感时,其社会地位已被彻底边缘化。在探索聚酯命运的隐喻背景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艺术的现状与未来也日益明朗。生成式AI通过自动化复杂的设计和创作过程,极大地释放了内容生产的潜力,也减轻了人工劳动力的负担。许多初创企业和小型公司借助这类工具创造广告及产品设计,大公司更视其为降低人力成本的战略要点。然而正如当年的“聚酯热”最终以文化审美的逆转告终,如今的AI艺术也正面临被贴上“廉价”、“缺乏深度”和“人工替代”的标签。如今全球任何人几乎都能使用这些工具,但正因其易得性,质量良莠不齐的内容充斥网络,造成视觉与听觉上的疲劳。
南亚及东南亚的低工资内容生产者积极参与AI作品的产出,虽对产量增长贡献巨大,却也导致整体艺术品质和原创性下降。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美的感知极具情境依赖,感性与文化因素难以被AI单纯模拟替代。技术从业者往往误认为AI艺术逼近人类艺术就具备高品位,但事实是AI作品往往是简化、重复和过时艺术传统的拼贴品,难免流露出“廉价合成品”的气息。生成式AI艺术如同聚酯面料一般,虽功能实用却缺乏情感厚度和身份象征的光环。这种“合成”的文化产品不仅在审美层面遭遇质疑,更在社会经济层面引发深远影响。首先,设计专才和创作工种面临被机器替代的压力,传统就业结构被重塑。
其次,生成式AI同样被用作传播假信息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其潜在恶意用途削弱了公共信息空间的信任基础。一个由同样技术生成的虚假图像驱动的产品设计,自然难以赢得社会尊重。现代社会处于后现代主义和信息过载的夹缝中。理论家曾预言媒体经济的发达将消磨人类的文化深度和价值体系,而事实正逐渐印证此类忧虑。市场对快速、廉价内容的追求使艺术和文化呈现出吞噬自我原创力的怪圈。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进化的新阶段,充当了“文化聚酯”的最新形态:易得、无限复制、缺乏差异性和身份认同感。
尽管如此,历史的轨迹亦指向希望。聚酯布料的终结证明人类文化的反弹力量总能重新点燃对品质与独特性的追求。人类天生追求真正的价值,艺术家和创作者在不懈探索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美学意义和社会符号。当文化的合成趋势到达极致,反向推动原创与手工艺的运动便会产生,引领我们走向另一波审美复兴。面对生成式AI的浪潮,个体及社会应保持警醒,拒绝盲目接受“便利合成”的诱惑。支持纯手工创作、本土艺术和原创设计,仍然是维系文化多样性与审美丰富性的关键。
未来的文化生态,将是合成与原创并存,科技与人文相融的复杂图景。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终点,而是文化变迁中的一环。只有深刻理解它的社会、经济以及审美影响,我们才能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浪潮中把握自己文化的方向,避免沦为“聚酯时代”的廉价消费者,而设计和创造属于人类独特灵魂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