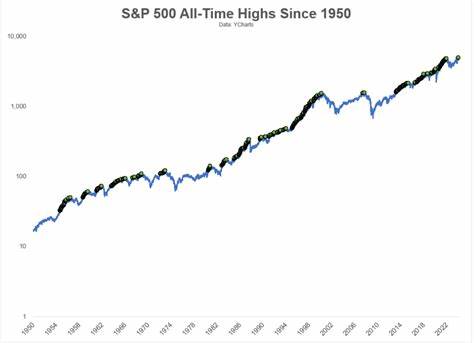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变革,从病毒式的聊天机器人到数十亿美元的商业估值,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到各行各业。然而,技术背后的伦理基础却显得薄弱且不足以支撑广泛的应用。AI技术的能力快速提升,但其可信度却常常无法得到保障,导致责任、安全与诚信等问题愈发紧迫,成为AI产业不可回避的现实挑战。 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过程中,伦理往往被视为附加的覆盖层,而非深植于系统结构的基础层。以IBM为例,部分团队正尝试打破这一固有模式,将伦理约束直接融入模型训练、市场推广及系统部署中。IBM的AI倡导负责人PJ Hagerty强调,AI不是构建“意识”,而是打造“工具”,因此应以负责任的态度对待人工智能,拒绝炒作和夸大。
AI伦理的真正难点,往往出现在最基础的模型层级。基础模型作为现代人工智能的根基,通过海量网络数据训练,孕育了大型语言模型(例如ChatGPT和Claude)。正如Hagerty所指出,基础层是模型“学到一切的地方”,如果数据中充斥垃圾信息,问题将始终无法根除。 由于基础模型设计为通用型,缺乏针对特定任务和约束,导致其吸收了大量有价值的语义结构的同时,也带入了网络上的有害内容、偏见和错误信息。这种黑箱特性使得模型的知识和行为难以完全把控和审计,甚至连开发者也难以准确预见其执行效果。这犹如一座用劣质混凝土浇筑的摩天大楼,短期内难见危机,但长远来看却带来结构不稳的风险。
在AI领域,这种风险表现为模型输出的脆弱行为、无意识的偏见或严重的误用后果。 斯坦福大学基础模型研究中心(CRFM)的研究多次强调,大规模模型训练带来的风险不可忽视,偏见传播、知识幻觉、数据污染和故障定位困难成为核心难题。虽然可通过数据筛选、过滤和治理等手段缓解问题,但无法彻底根除。这凸显了早期设计阶段的重要性,选择优质数据和明确治理规则成为打牢伦理基础的关键环节。 此外,企业所宣称的“人工智能”内涵常常含糊不清,造成市场和用户的误导。Hagerty指出,不同团队对“AI-powered”的定义各异,很多所谓的智能系统实际上是自动化流程、决策树或简单的条件判断,因而夸大宣传带来“炒作泄漏”现象。
这不仅令用户和投资者产生错误预期,也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行业信誉。尤其是金融、医疗等监管严苛的行业,误认AI具备超出实际能力的判断,可能导致不应被机器替代的关键决策权被错误转交,责任归属模糊成为潜在风险。 那些追求新颖且缺乏有效应用场景的AI项目,更是浪费大量计算资源,甚至以“进步”之名蒙蔽人们视线。Hagerty对此直言不讳,举例说明部分企业盲目使用大型语言模型进行时间序列预测——该领域传统统计方法更准确高效——既不合适又效率低下,象征着对AI能力的误解和滥用。 除技术层面误用,围绕AI的替代焦虑也需理性看待。许多公众担忧AI可能取代律师、教师、程序员、作家等职位,但事实更真实、具体——AI工具主要替代的是重复性劳动,而非创造性岗位。
诸如watsonx代码助手、GitHub Copilot等辅助工具,擅长生成标准代码块、建议模板代码和提升开发效率,能够帮助新人更快入门,资深工程师专注架构设计。这种“任务替代”带来整体效率提升,是技术进步的正面体现。 然而,基础模型所基于的开源网络数据仍存在大量问题,例如安全漏洞、过时的编程习惯、版权争议以及难以察觉的隐患。这意味着模型生成的内容可能继承并放大这些缺陷,强化了对人工审核的需求。工具固然能辅助提升效率,但开发者仍需对最终成果承担责任,确保质量和安全。 除开发层面外,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也不容忽视。
近十年前,微软发布的Tay聊天机器人被恶意操控,迅速发表攻击性和阴谋论内容,最终下线道歉,成为AI安全失败的经典案例。如今,虽有更多企业加强过滤、分类、提示清理和强化学习以防止此类事件,但这些措施多聚焦于表面问题,如语言语气和粗俗内容,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风险,如提示注入和恶意用途。安全应被视为整体设计问题,即是否考虑到模型可能的误用、内容脱离上下文、输出被过度信任等安全隐患。 对于生成图像、视频和声音克隆等多媒体操作工具而言,安全并非单纯技术准确性,而是涉及认知与社会影响。逼真的输出不仅改变人们感知,还可能影响记忆、判断与归因,甚至引发信息混淆和信任危机。面对此类复杂场景,设计者必须深入考虑输出内容离开系统后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及受众认知。
AI治理机制亦是构建伦理支柱的核心部分。快速发展的技术环境中,治理常被误解为进度拖累、繁文缛节或模糊不清,但在Hagerty看来,治理是构建可信AI的必要基础。就像软件开发不会发布未经测试的代码,人工智能模型同样不能未经审计便匆忙上线。 IBM的watsonx.governance等工具为团队提供了追踪训练数据、模型变更与异常检测的能力,既符合监管要求,也保存了开发过程的“记忆”,利于诊断、回溯和纠偏。良好的治理能被视为AI的版本控制,保证模型在演进过程中的透明度和可控性。 现阶段,“机器遗忘”技术也开始崭露头角,能够部分移除问题数据或行为,而无需重新训练整个模型。
这一技术体现了以修正和适应为导向的思维转变,目标从打造完美模型转向打造可以修正、负责任的模型。尽管无法完全消除偏见和安全风险,但通过科学严谨的流程区分可接受的失败和疏忽的伤害。 Hagerty建议将伦理审查纳入产品规划周期,而非仅作为发版检验环节。利用像IBM的AI公平360、Granite Guardian和ARX等工具,提前识别潜在偏见并进行红队测试,排除边缘案例,确保部署后系统能够安全、可靠地工作。伦理不仅仅是为了避免伤害,更是塑造积极影响的设计原则。 他强调,完美的系统不存在,但可打造的是“缓慢失败、可预见性强”的模型。
道理在于把伦理作为设计理念,提升软件质量与透明度,设置合理用户期望,最终实现更有价值的产品。 对Hagerty而言,真正令人振奋的AI并非科幻中的通用智能或严肃的政策框架,而是像代码助手这类实用工具。它们降低阻力,不夸大自身能力,专注于实实在在的价值,成为未来AI应用的典范。 他期待看到一个“无趣”的AI世界,即实用、专注且诚实地展现自身功能。这并非意味掩盖野心,而是清晰定义野心所在,追求可靠性而非惊喜,打磨在真实环境中表现出色的系统。 AI的演变不可逆转,工具将持续更新,用户的期望也会随之提升。
最终能够成功的团队,将是那些技术实力与伦理自律并重的群体。因为只有这样,AI才能真正实现它的潜能,成为改善社会和推动进步的有力工具。